我在一个如火的夏季认识她
她穿着米黄色的裙子
烫着卷曲的头发
描了眉毛还涂了口红
她突然出现在我的世界
我毫无戒备的
坠入一场意外的爱情
我们在下一个如火的夏季分别
她穿着白色的裙子
烫着卷曲的头发
描了眉毛还涂了口红
在学校东门的小餐馆
我们喝完了最后一杯故事
然后从容离开
这是一场莫名的爱情
她告诉我她起码连心动
都不曾发生
哪怕一点点
哪怕一瞬间
这是一场纯洁的爱情
纯洁到和爱有关的一切
都不曾发生
哪怕是牵手
哪怕就一次
这是一场虚无的爱情
我甚至开始怀疑它只曾
在幻觉中发生
没有纪念物
也没有佐证
我曾构思了无数种重逢
每一种都充满浪漫与感动
而真正的重逢
却简单而匆匆
三年后的一个傍晚
在泰山脚下的一个饭馆
我们以面对着面吃饭开始
以一声再见结束
我记得我的脸喝得酡红
她始终保持着笑容
我说了很多话
她一直保持倾听
她抢着要付账
而我更愿意
为这段虚无的爱情埋单
我不敢承认我曾爱上了她
我宁愿相信她只曾出现在梦中
不管曾经的记忆与冲动
多么清晰分明
我仍然只能相信
这只是一场
虚无的爱情
从来都不曾
真正发生
2008年1月6日夜于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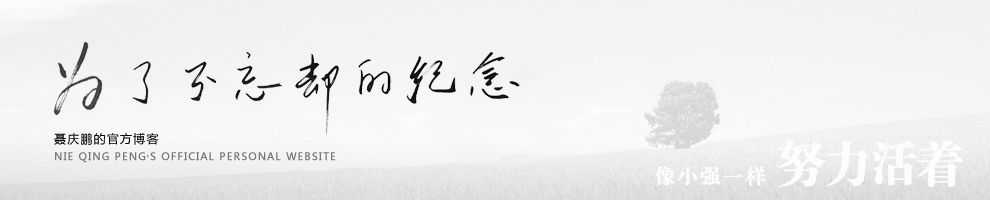
 已有3人评论
已有3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