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洗手间
拿着钳子
铛铛铛铛修水管
我的女人在厨房
拿着刀
铛铛铛铛剁饺子馅
2008年10月4日 黄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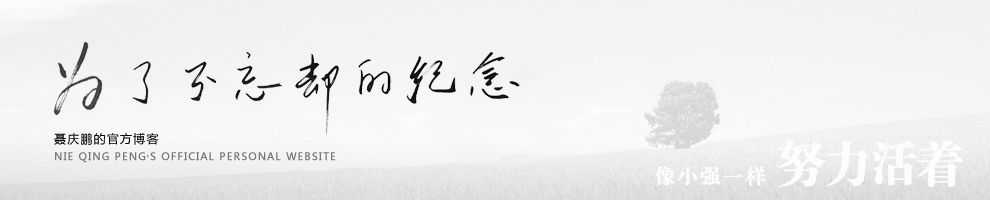
我在洗手间
拿着钳子
铛铛铛铛修水管
我的女人在厨房
拿着刀
铛铛铛铛剁饺子馅
2008年10月4日 黄昏
 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 他喜欢
闭起门来造车
自行车 摩托车 甚至汽车
他都想试一试
他对车没有研究
也并不以此为生
但却爱此不疲
他第一次见到车
就明白了所谓车
就是一个安装了轮子
可以载着人跑的盒子
从那以后
所有的车
在他眼里
都不过是一辆车而已
没人知道他为什么
非要闭起门来
他对此讳莫如深
一如造车的过程
在完工之前
任何人都不准窥视
包括他的老婆
很多年来他坚持不懈
造了一辆又一辆
他把车藏在一个偏僻角落
每当夜深人静
就推出来反复擦洗
然后驾着它
在自己的院子里
转来转去
每当我调侃起这个嗜好
他都一本正经
甚至有些激动:
每个人都应该自己造辆车
难道不是吗?
——你要不要造一辆?
我每次都忍不住想笑
但他的表情很严肃
一点都不像开玩笑
08年9月21日午
每七百块煤
就有一块是红的
就是那种血红
血一样的红色
这样的煤
挖掘的时候
分外容易
每年都出产大量
越小的煤矿
越贫瘠的地方
挖得越多
这样的煤
运输的时候
分外沉重
一块仿佛千斤
仿佛无以承载
红煤也有亲人
他们不舍得离开
这样的煤
燃烧的时候
分外激烈
那火苗分外高大
那热量熔化一切
那声音震人心魄
不是噼噼啪啪
仿佛呜咽
又仿佛呐喊
这样的煤
烧成灰烬的时候
分外纯净
仿佛人的骨灰
一样的灰白色
一样的重量
只是没有被安葬
而是倾入垃圾堆
书上说
煤是远古植物变化而成
红煤一定不是
红煤的产生过程
和这些黑煤一样
黑。
2008年8月1日 建军节 痛悉河南禹州再发矿难
一个幸福的人
过着幸福的生活
有一天
天上突然掉下许多钱
大家都去抢
大家都抢了很多
而他没抢到
他很生气
气死我了
去他娘的幸福
我现在只想知道
凭什么那么多人
就我没抢到
龌龊的张三
卑鄙的李四
恶心的王五
他们都抢到了
凭什么我没抢到
我吃了大亏了
气死我了
一个不再幸福的人
过着和以前一样的生活
所谓正直
是痛苦之树结出的毒果
外表光鲜无比
毒性足以致命
奇怪的是
总有人愿意吞下
更奇怪的是
吞下这毒果的人
没有一个后悔
这是一枚有魔力的果子
总有些人被它吸引
向着痛苦义无反顾
这很像是一群傻子
捧着果子贪婪地啃咬
似乎跟本就不知道
这是一枚毒果
然后
或口吐白沫
或满地打滚
或当场毙命
但总有人乐此不疲
他们
爱上了中毒
2008年5月24日于大雾的清晨
那样的时光
那样的世界
那样湛蓝的天空
那样清澈的河水
那样年轻的我们
那样的花香
那样的你
那样透明的脸庞
那样的花团锦簇中
那样羞涩的说出口
那样灿烂的笑容
那样清澈的眼眸
那样傻傻的等待
这样的日子
这样的未来
这样四角的天空
这样陌生的表情
这样疲惫的我们
这样的天涯
这样的我
这样朦胧的记忆
这样淡淡的怀念中
这样沧桑的说出口
这样迷人的花香
这样不变的河水
这样伤感的心情
那时的微风悄悄地吹散
阳光灿烂的笑语
那时的我们痴痴地演绎
流水潺潺的故事
那时的落日很美很美
梦想很遥远
那时的我们很傻很傻
幸福很简单
那时的旅程很短很短
我们肩并肩
那时的热情很烫很烫
今天仍温暖
你会回来吗?
你会回来吗?
2008年4月18日 晚春的午后
是谁收殓了
心灵的尸骨
却无处收藏
用世俗做铁锹
掘出一个洞穴
利利索索埋掉
应该有一座碑
有一段墓志铭:
一个不该死的人
死了
还要留一个洞穴
孤独的躯体
早晚要与他合葬
2008年3月30日夜
伟大的科学家们
激动的宣布
他们发现了传说中的天使
虽然仅剩一副骨架
一副三百五十万年前的骨架
他们说这是真的
这多么让人激动
我看到这照片
忽然忍不住流下泪来
——天使死了
08年3月27日闻南非发现天使化石
我看到一个人
他用一种奇怪的方式走路
他用六条腿走路
两条是腿
两条是手
两条是拐棍
少了任何一条他都寸步难行
不仅寸步难行
甚至连站都站不稳
他用另外一种奇怪的方式移动行李
行李是两个小包
用绳子捆在一块木板上
木板下面有四个轮子
在前进时
他用一根棍子撑着地
用另一根棍子奋力拨动木板
于是他可以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
踉跄前行
人们纷纷躲开
仿佛躲避瘟疫
也许是不愿沾到晦气
或者怕那木板车撞到自己的脚
这都是一些多么高雅的脚啊
怎么能被如此龌龊的木板撞到
我无需躲开
因为他并不是向我走来
我穿着鲜红的西装
打着鲜红的领带
还有油亮的皮鞋
以一种优雅的姿态
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
以一种高尚的怜悯情怀
为他构思一首诗
我看见一个女人
具体说是一个老妇女
精确的说是一个胖老娘们
她走上前来
一把抱起了木板车
走下长长的台阶
红扑扑的脸上盛开着微笑
人群都在看她
仿佛观看一种表演
但这不是表演
她确实抱着这木板车
一直走到出站口去
这打断了我的构思
并让我感到难受
我感觉此时此刻
坐在这里观察并不高尚
虽然我同情他
同情到快要落泪了
我想我应该站起来
我想一个以奇怪方式走路的人
会以一种更奇怪的方式下台阶
但是这次
我并没有这样的好奇心
等着去
欣赏
2008年3月6日午
我认识一个人
名字叫八亿
这个名字很有气派
不过人却寒碜的多
朱门的酒肉臭了五千年
他到今天还吃不饱
大厦千万千万间
他的土屋快要塌了
而且最最重要的是
他是一个哑巴
他曾经会说话
甚至也很健谈
他说他爹打过鬼子
他哥消灭过反动派
他老婆给红军编过斗笠
还给解放军喂过奶
那送粮的小车渡江的船
和墙上的光荣户都还在
不过这些都是往事了
现在他只会
种粮种菜和养猪
八亿今年五十九
有的人到了五十多岁
就可以满街溜达
遛鸟和养花
而且还有钱拿
八亿五十九了
还在种粮种菜和养猪
他的故事早已没有人听
政客学者和成功人士
甚至连村口的狗
都只愿意和富人说话
没人愿意听他说话
早已习惯了没人和他说话
于是他成了哑巴
没人关心他成了哑巴
他们只关心他是否能够
把种出的粮食蔬菜和水果
及时送到城里
当然不是白要
钱总是要给一点的
正是有了这种慈悲
八亿虽然半死不活
但总算没有死
八年前我逃离了八亿
我不愿意象八亿一样种粮食
我却每天都吃八亿送来的粮食
我努力使自己变得高贵
却欣欣然地忘记了
中国还有一个八亿
等我察觉到这一点
我发现几乎所有人
都犯了和我同样的错误
八亿成了哑巴
人们便都在说
八亿真是一个好人啊
八亿是我们的兄弟!
他们问八亿
你富裕吗?
八亿不说话
你幸福吗?
八亿还是不说话
于是他们向全世界宣布
八亿是幸福的
好一个幸福的八亿啊
好一个幸福的哑巴!
他在幸福中沉默着
我知道其实八亿有话要说
我甚至知道他想说什么
我也知道他——八亿
这个人见人厌的乡下人
这个穷了五千年的贱民
一定还会说话
虽然他已经哑巴了这么多年
一定还会说话
不需要任何人代替
他完全有这个能力
为自己说话
当这一天来临
我们都要虔诚地跪下来
一字一句的
认认真真地
听。
2008年1月17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