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忽然想起一个早年的梦中情人
忽然想起了,便抑制不住
思念决堤,无处可藏
辗转找到她的号码
电话那头,她的声音还那么熟悉
让我骨头酥软就像十年前
而她,却已听不出我
我很认真地说:我向你表白思念。
她只是淡淡地说:你都结巴了。
我何止结巴了
我简直就是个哑巴
2010.7.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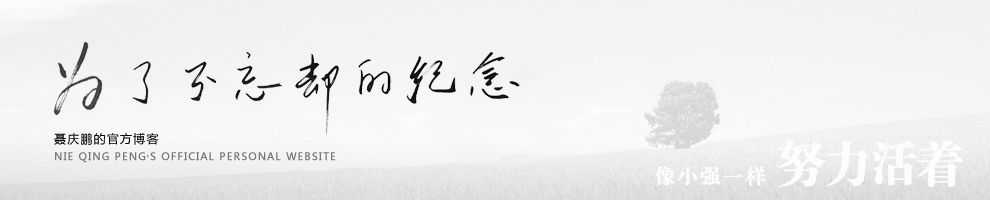
我忽然想起一个早年的梦中情人
忽然想起了,便抑制不住
思念决堤,无处可藏
辗转找到她的号码
电话那头,她的声音还那么熟悉
让我骨头酥软就像十年前
而她,却已听不出我
我很认真地说:我向你表白思念。
她只是淡淡地说:你都结巴了。
我何止结巴了
我简直就是个哑巴
2010.7.14
 已有3人评论
已有3人评论 《麦收心得》
我们在丢弃秸秆时
毫无愧意
虽然它曾哺育了麦穗
于是我知道
卸磨杀驴也是自然法则
《击杀蚊子》
每晚我都要在睡觉前
奋力击杀蚊子
起初是因为没挂蚊帐
后来挂上了蚊帐
我却已迷上这项活动
一巴掌下去
粉身碎骨
一个不留
这帮喝血的畜生
《拯救知了猴》
我试图从饭店的厨房里
拯救一名知了猴
起初我只是拿来把玩
后来看到它的狱友
一声不吭地下了油锅
变得金黄酥脆香喷喷
而它又在我的T恤上
很努力地攀爬
多么憨厚的动物
我动了恻隐之心
解救行动易如反掌
我将它带出了饭店
顶着烈日四处寻觅一棵树
最好是杨树
最好远离路边
它趴在我的肩头
一动不动
我走得很小心
生怕它跌落
2010.7.13
这无疑是这个博客创建以来最慢的一次更新。
整整一个月。上一篇日志是在6月1日的深夜完成,而今天正好是7月1日。这创造了一个纪录。其实我无意去故意创造这个纪录,我本来想赶在6月份的最后一天一定补上一篇什么,好达到平均半个月一篇的底线,然而这么小小的一个心愿在弄人的造化的面前也成了奢望——也就是在昨天下午,6月的最后一天,我将呕心沥血开发了一个多月的软件发送给了客户,卸下了压在心头很久的一块石头,正在盘算着晚上回家好好梳理一下思绪,写点什么的时候,一个电话“及时”赶到——有台服务器瘫痪了。
我一直觉得从事服务器管理工作就相当于坐在不定时的炸弹上,爆炸时间是随机的。这台服务器上有大小二十多个网站,而且有几个重要的网站,瘫痪半小时后我的电话就成了热线。赶到机房后,初步判定是因为空调故障导致无法制冷,进而导致服务器机房温度过高,进而导致服务器硬件烧坏。至于哪个部件烧坏无法确定。打HP的客服电话,说已经下班了。万般无奈,在闷热了机房里挥汗如雨,折腾到半夜,无功而返。这台服务器的数据已经5个月没有备份,一旦丢失,后果不堪设想。在这样沉重的压力下回到家,茶饭不思,草草吃了两块西瓜,算是晚饭。然后又四处打电话求助,又上网搜索,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博客,显然是不可能的了。好在上天有好生之德,没有往死里逼我,今天早上我又认真对照服务器说明书,依次试换了CPU、PPM等之后,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给CPU供电的稳压模块坏了。没办法,拆东墙补西墙,从另外一台基本闲置的服务器上取了件,更换之后成功开机——在看到熟悉的Windows启动界面的时候,我在机房里蹦了好几下,兴奋地像个孩童。虽然只是虚惊一场,但上天跟我开这样的玩笑,未免过于残忍。
六月很忙。公事私事都是如此。繁琐的工作天天排满日程表,疲于应付,晚上回到家还要开发一套软件,这套软件是以前给市政府开发的一套公文系统,这次是升级,颇费心血,时常通宵达旦。而且这个六月又是狂躁溽热,炎热的天气和世界杯都来捣乱,分散去我许多精力。我在凌乱的生活中送走了六月,而且六月的最后一天都不肯放过我,而以这么有意义的方式结尾。
当然并非没有好事,比如书的稿费到了。2007年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PHP教材,当时签了个合同,每销售一本提成百分之八,在第一版4000册售完之后结算了一次稿费,之后便没了动静。我也忘了这码事,甚至连合同都在去年搬家时丢了。前段时间,本书的另一位编者,就是那位在我博客中出现过的“二鬼子”,他在市场上发现这本书已经第四次印刷,印到一万多册了。我赶忙询问出版社,得知可以继续结算第二次和第三次印刷的稿费,交完各种手续费,再交完高达14%的个人所得税之后,三位编者分成,我还有三千多的收入,这不算一笔大钱,但收钱总不是坏事,尤其是在我正为对抗炎热而准备筹资购买一台空调的时刻。
六月里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回家收麦子了。今年比较特别,母亲要照看楚涵走不开,姐夫又不慎砸伤了腿无法下地,于是麦收就成了大问题。虽然只有一亩多地,单凭父亲一个人,还是无法完成的。即使可以自己收割,脱粒这个环节也是需要人手的。况且收割之后还要立即种玉米,然后还要种水稻。于是趁着端午节的三天假期,我决定回家帮父亲收麦子。我已经整整十年没有进麦地,重新又操起镰刀,竟还十分熟练。唯一不足的是体力。头一天下午割了2分地,还是能应付的。但是第二天,也就是整个六月里最热的那一天,早晨四点半起床,割麦、种玉米直到晚上11点脱粒完毕颗粒归仓,我这一天里流的汗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我和父亲两个人种了3分玉米,割完了一亩地的麦子,并一捆一捆地从地里背到路上,装上地排车拉到打麦场,全部麦子运送完毕是在晚上9点,正当我们准备回家吃饭的时候脱粒机又到了,没办法又坚持完成了脱粒,最后我骑着三轮车往家走的时候,筋疲力尽。曾经当我在深夜里揉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强打精神编写程序的时候,我以为这是天下最难的工作。然而当我站在炎热的麦地里筋疲力尽口干舌燥腰酸背痛而前面的麦子还是一片一片望不到边的时候,我感到深夜里听着周杰伦编写程序是那么惬意。最难的还是农民,天下的罪,农民受了多半。就像我那五十七岁的父亲,干瘦的他拉着近千斤的地排车在崎岖的田间小路上挥汗如雨地前行,遇到一个上坡,他会尝试好几次才能上去。二十八岁的我拉不动这车,五十七岁的他拉得动。我曾多少次地想对他说:“你不要种地了!”但是我知道,说了这句下面必须还要跟一句:“我养着你”。但后面这句我还不敢说,我还没有这个能力。望着奋力拉车的父亲的背影,我只能放任无尽的惭愧将我吞噬。
最后要说一件事,我想楚涵了。回家收麦的时候,母亲也要回去看看,说至少可以帮着烧水做饭,于是便带着楚涵一起回去了。我只在家呆了两天便返回日照,楚涵留在家里快二十天了。最近的几晚我连续梦到她,梦到她清楚地叫我爸爸。有一次我梦到她摔倒了,而且是向后仰倒,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回家,母亲说她昨天晚上果然摔倒了,而且果然是向后仰的。我虽然不太信鬼神但我相信人的某些精神活动还不能完全被科学解释。第六感也许真的存在。我想她了,我会说,我想我女儿了。而楚涵也一定会想爸爸,只不过她不知道怎么说出来。但是她想了,所以我感觉到了,我相信这个,而且是笃信。电话催了无数次,她这个周末就要回来了。我昨晚梦到她回来了,而且没有晒黑,小脸还是很白,咯咯地笑声还是那么纯洁,我是真的想这个小家伙了。
六月,好忙乱的一个月。我累了。
2010年7月1日
我听到她的故事,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和朋友在小酒馆临窗而坐,雨水潲到玻璃幕墙上,流淌成一道水帘。马上路车辆稀疏,霓虹灯被稀释成模糊的成一片,看不太分明。
酒过三巡,朋友揉了揉发红的眼睛,问我:
“你知道小A吗?”
我摇头。他长长地“唉”了一声,眉头紧起来。
“死了,去年死的,二十七岁”。
“长得挺俊俏的,我记得你见过的——你真的不记得了吗?那年你回家,在咱村后面的路上,我指给你看过的。模样挺好看的,也不胖。脸常年红扑扑的——因为有心脏病,春天的时候脸最红,冬天就喘地厉害。”他伸手比划着,看我一脸茫然,有些着急的样子。
“你知道的,杀鸭那种地方,除了小伙子就是老娘们。年轻的不多,她算漂亮的吧”。
“她在那干什么活?”
“洗鸭肠吧,开始是让她拔毛,她没劲拔得慢,后来就去洗鸭肠了。很臭的活儿——不过不沉,杀鸭这种地方,放血、拔毛、开膛,没好活”。
“几个老娘们给她介绍对象,介绍了好几个,有一个差点成了。谈了好久,差点要定亲了,后来还是又喘,喘得厉害,人家就不要了。这样的情况,你想想,确实没办法的。你说谁敢要?可惜了,天天有说有笑的,先天心脏病,可惜了。”
“因为心脏病死的?”
“不知道。光听说死了,许是这个病吧。这种病,什么活也不干,天天养着,许能多活两年——才二十七,没想到死这么快。”。
“对了,她的尸首,你知道吗?她的尸首卖了。卖了八千块钱。”
我一口菜堵在喉咙里,惊地说不出话:
“卖了?”
“卖了。跟外面说是卖给医院做实验去了,其实——你知道么,听说是卖给人做媳妇了。外面村,挺远的村,有个小伙死了,活着的时候没对象,他家里人买了尸首,埋在一块,给他做媳妇去了。”
“他爷早死了,他妈老实,没什么主意。村里人都说,人都死了,就是埋了早晚也是烂掉,不如卖了吧。卖到那边也是埋,还有个作伴儿的。她妈就答应卖了。于是就卖了。”
我捏着酒杯,转来转去,不知道该说什么。朋友叹一口气,一饮而尽。
我听到她的故事,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繁花落尽,零落成泥。我望着窗外的风雨,我想着某片荒野中的某处坟地,她埋在那里,身边躺着一个陌生的男人。那雨水透进她的棺材,一定是极冷的,冰冷冰冷的。
窗外的大风摇晃着刚迎来初夏的小树,几乎要折断的样子。
不,有的已经折断了。
2010.5.31 深夜
《神经病》
即使我把自己
也装成神经病人
仍然没法和他们交流
我虽然佯装倾听
还会不断点头
但我毕竟不是病人
听不下去的时候
忍无可忍的时候
我会喊一声
真他妈神经病!
然后愤愤离开
他们虽然有病
这句话却听得懂
所以很多时候
我都是在背后
小声地说
《酒与智商》
我发现每喝醉一次
智商就会下降很多
但我还是依赖酒精
麻醉躁动的灵魂
也许我在有意将自己
变成个傻子
《墨镜》
我明白了为什么
很多人喜欢戴墨镜
这样看到的世界
才更真实
《阿兰》
昨晚又梦见阿兰
自从喝下你的笑靥
我已沉醉六年
2010.5.23凌晨
昨天修改了一个QQ签名,本是无意之举,不料却引来了一些围观。有的朋友问我,你这签名啥意思啊?有的朋友则说,你这签名太悲了,有些消极。还有朋友说,你这签名很吓人。不过没有一个人说这个签名很深刻——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这句话不是我的原创。这是鲁迅先生的散文集《野草》中的一篇《墓碣文》中的句子。我不记得何时看过这篇文章,也忘记了大部分词句,只是这一句话记忆深刻,昨天无意间想起了,便做了签名。我知道,如果我在后面加上“鲁迅”两个字,就一定有人会说这句话很深刻了——我简直做过这样的试验。我曾把自己写的句子念给别人听,说是某大作家写的,他们便连声称好,甚至能分析出一堆深刻的道理。或者我把一些名人的句子念给他们,说是我自己写的,他们则完全不屑一顾了。我知道了文学也是讲究出身的。就像这句话,倘若是我说的,便一文不值了,但它偏偏是鲁迅大师的手笔,也许是现在读鲁迅的人也确实少了罢,因此围观的人才这么多。
这是一篇十分怪异的文章。也是鲁迅先生的散文(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首散文诗)中公认的最难理解的篇章之一。在写这篇东西之前,我从百度搜到全文,念给LP听,问她怎么样,她想了一想,说:鲁迅写文章有时候也跟说梦话似的。说完便转身去看电视去了。电视里正在播新版《三国》,也许那个比这篇文章有意思得多。我本想指出她的肤浅,但转念之间,却发现她未必错了。鲁迅先生正是描写了一场梦境。文章的一开头便是“我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可不就是做了个梦吗?我惊喜地发现这也是对这篇文章的一种解释——当然这只有十万分之一的可能。我相信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必然是多梦的,而且他们的梦也一定是足够荒诞离奇的。所以这未必不是鲁迅先生在梦境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后的产物。当然在无数分析家、研究家的眼里,鲁迅先生这么伟大的文学家,不会去简单地记述一个梦境而不添加批判讽刺与忧国忧民在里面。
关于这篇短文的主旨,数十年来一直有人在研究,观点各不相同,有的观点甚至完全相反。我一直有一种观点,很多文学研究家们在研究古人的文章的时候跌入了历史的陷阱。他们更多地喜欢讨论历史而不是文学本身。我知道在欣赏某些文学作品的时候适当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作者个人处境是非常必要的,但很多研究家们的研究已经显然走火入魔,他们不认为文学可以明白如话,任何一篇文章如果没有三万字五万字的解读便是肤浅和错误的。他们忘记了“子非鱼”的典故。他们自以为了解历史,用记录在案的那一点点历史的碎片去试图还原作者的本意。他们更喜欢去抽丝剥茧般地、一厢情愿地、自以为是地分析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却不愿意去挖掘这些能够在成百上千年中感染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境遇下的人们的经典文字中的文学美感和某种普遍地代表性。他们一说起鲁迅便要把他的一切作品打上忧国忧民、针砭时弊与拯救民族的烙印,而不愿意去琢磨在国民党反动派早已经零落成尘的今天为什么还有人喜欢读这样的文字。一切不朽的作品必然具有穿越时空能力,它带给人们的共鸣可以持续千年,完全不受历史的局限。将文学欣赏人为复杂化,是这帮研究者最大的贡献。研究宏观的历史可为今人借鉴,微观的历史仅供学者谈资。而因文学欣赏而研究微观到作者写作的当天吃过什么饭拉过什么屎放过几个屁的历史,则完全是迂腐文人们为了标榜自己的深刻而发明的蒙汗药。让人晕晕乎乎然后情不自禁地说“有深度”就是他们的追求。
鲁迅是因为时人以及后人对其文章的喜爱和认同而成就其伟大。而并不是在评论家们的“深刻”解读中伟大起来的。这些自以为可以分析鲁迅作品并自封正确的人,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可以超过鲁迅。他们何以有信心可以把将近一百年前一位思想巨人在写作时的感情看穿呢?他们何以敢去做这样的尝试呢?今人读鲁迅之作品,若能学得文字技巧之运用一二,词句章回之组织一二,抑扬褒贬之轻重一二,文学良心之要义一二,天下兴亡之忧喜一二,再有文字之学之优美、犀利、酣畅与精准一二,足矣。倘能在先生的某段文字中察觉到某种共鸣,似诉心中无限事,那便是令人激动的意外之喜。除此之外,概无其他。至于先生写作时的来龙去脉如何,所思所想如何,所作所为如何,真的不必追究,也不可能追究。倘若非要把这种追问说成一种学问,顶多只能算是一种“好奇心”学问,自娱尚可,唬人就不对了。
我忽然又有一个重要发现,且看先生在这篇《墓碣文》中的另一句话: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不妨抛开这篇文章的整体,单就断章取义地把这一句话当成一个比喻。自己品尝自己的心,刚挖出来时,身体剧痛尝不出真正味道。而痛定之后慢慢品尝,心却已经陈旧,怎能尝出最初的味道。先生之心,自己不能得其味,更忧后人不能知其味。后人即便品尝一二,也是“陈旧”之心,岂是先生本味!自知无人可知其本味,先生释然曰:“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任由一个个不能“答我”的路人走过他的墓旁,他是在释然地微笑着的。
必须再次强调上面这段以及之前的“梦境”论并非我对这片《墓碣文》的全部理解,只是我在随手填补一个个十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不论是什么文章,对于读者而言都无需被限制在一个标准答案式的狭小的理解空间里。这也是我对语文教育中所谓“文学欣赏”题一直十分抵制的原因。记得某名人曾经说过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我们老祖宗也常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些原则对于文学欣赏尤其重要。倘若一篇文章只能有一个主旨,只能按一种方式去理解,只能在同一个点上产生共鸣,那无疑是可笑之极、荒唐至极直至悲哀至极的。这种做法是对教育的亵渎,对文化的犯罪。喜欢一篇文章,一万个人可以有一万个理由,哪一个理由才是“本味”?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可以有学派之分、主流与非主流之分、普遍与个别之分,但不应该有对错之分。科学的词典里没有“也许”,艺术的书本上没有“肯定”。所谓文学欣赏的标准答案,是对思想的禁锢,艺术的扼杀。
但求爽口,莫问本味。我感受到先生这篇文章的深邃,又感受到它散发着一种难以捉摸的神秘气息。这种气息吸引了我。也许只是那一句“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吸引了我,让我时时回味。我讲不出道道,也说不出历史,哪怕这篇文章不是出自鲁迅,哪怕出自一个无名小辈之手吧,也足以为我吸引。其他所有喜欢这篇文章的人未必都是像我一样的感受,让他们记住这篇文章的原因可能千差万别,这正是这篇文章的魅力所在,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先生的魅力所在。倘若一定要站出一个权威定出有一个本味,倘先生在世,料亦不能容。
不求本味并非不求甚解,本味非解,本味无解。
2010年5月12日深夜
附:《墓碣文》
我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读着上面的刻辞。
那墓碣似是沙石所制,剥落很多,又有苔藓丛生,仅存有限的文句——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
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离开!……
我绕到碣后,才见孤坟,上无草木,且已颓坏。即从大阙口中,窥见死尸,胸腹俱破,中无心肝。而脸上却绝不显哀乐之状,但蒙蒙如烟然。
我在疑惧中不及回身,然而已看见墓碣阴面的残存的文句——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
我就要离开。而死尸已在坟中坐起,口唇不动,然而说——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
鲁迅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楚涵一周岁了。
一年前的今天,4月30日,在我焦急的等待中,她呱呱坠地。转眼间,她一周岁了。一年的光阴似乎是飞走的。我,以及我这个家,似乎都和一年前没什么两样。而她,楚涵,却日新月异般地生长。她今天已经可以独自站立,在大人的搀扶下健步如飞,她几乎会走路了。她已经可以清晰的说出好几个事物的名字,可以清楚地叫“奶奶”和“妈妈”。她学会了在别人说“拜拜”的时候向人挥手,她可以指出家里大部分电器。她已经学会撅着小嘴亲吻别人,她几乎是一个大孩子了,起码我是这种感觉。
她对我分外亲切。也许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很少在家的缘故,她见到我总是兴奋异常,张开两个小手让我抱。一直感到渺小而单薄的我,从未感到谁对我如此的依赖。楚涵让我感到了力量,一种庇护别人的力量,虽然只是庇护一个孩童。这样我非常满足,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对于别人的意义。
我没有给她买蛋糕,也没有给她买什么礼物,但我从心里隆重地祝福她,我的女儿,楚涵,生日快乐。她今天似乎也格外兴奋,一整天都笑呵呵地,她可能不知道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一个伴随她一生的日子,但她似乎分明又第六感,让她异于平常。以后的每一年,这一天都会有所纪念,不论是采取何种形式。就像她的第一个生日,我以这么一篇短短的文字纪念一样。
她会在未来继续带给我无穷的惊喜,我深知这一点。虽然她现在还不会喊爸爸,但我早已体会到一个父亲的幸福,这从去年的今天她诞生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她总是持续不断地给我带来的惊喜和幸福感,她让我随时都充满期待,这种感觉伴随我每一天。我说过她这一生会有无数个第一次,就像今天过第一个生日一样。她让我甘愿以自己的燃烧来温暖她,以自己的沉重来轻松她。我希望她是幸福的,哪怕以我的幸福为代价。
我爱你,我的女儿。

2010年4月30日夜
你我有否见面?
可曾在梦中相见?
偶尔谈笑间,
一丝过往乍现。
可叹,可叹,
流年诲我不倦!
——二鬼子《无题》
二鬼子是我一个朋友。我之所以称他为朋友而不称他为同学,是因为我同学有很多,但不是每个同学都可以称为朋友。二鬼子是我无数同学当中很少的好朋友之一。
“二鬼子”显然是个绰号,这个名字的诞生十分曲折。我只记得最初和他交往,是因为他爱看《电脑报》,是班里很有名的电脑高手。大概这个世上才貌双全的人并不太多,所以他和我一样,虽然有才但其貌不扬。那时候的他个子不高,身体消瘦,头发和胡子时常很蓬乱,穿着也十分土气,不仅土,而且还有些脏——大概就是非常不修边幅的一个人吧。这个形象说的严重一点是有些猥琐的,倘若戴一顶日本军帽,确实是像个鬼子的。
不过这并不是他绰号的由来。那时候他喜欢踢球,喜欢一个叫“VERON”的意大利足球明星,翻译成中文大概是“贝隆”。那个时候刚流行上网,他便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叫贝隆。但是大家似乎并不认可这个名字,他不论是形象还是球技都和贝隆相差甚远,于是逐渐演变成了“贝鬼”。“鬼”这个字总有些贬义吧,但绰号倘若不包含贬义就不叫绰号,叫雅号了。后来大概由于他在宿舍排行老二,“贝鬼”慢慢演化成了“二鬼”,最后便成了“二鬼子”。似乎曾有人试图再将其演化成“二狗子”,但失败了,“二鬼子”一直沿用到毕业。
二鬼子是一个才子,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若不是如此,我们也不会成为朋友。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个穷人。大学里面也有贫富分化,穷人只愿意也只配和穷人交往。我愿意和每顿饭花2元钱以下的所有人交朋友,二鬼子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家境似乎比我还好一些,起码不用经常像我一样借钱度日。他老家在沾化,一个盛产冬枣的地方。依赖着冬枣的收入,他每年的学费还是有着落的。不像我只能依赖银行的贷款。我们时常一起出入在学校北门的地摊,去喝免费粥吃廉价的饭菜。我的脑海中仿佛又浮现出他穿着灰白色破旧西装,红色的毛衣,原本蓝色但是因为太脏而变成蓝黑色的油腻腻的衬衣,行走在大街上的情景。若不是鼻梁上的那一幅眼镜,真的很像一个叫花子。
当然穷并不是我选择朋友的唯一标准,我喜欢穷而且乐观而且坚强而且热情而且善良而且朴实而且上进的人。二鬼子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的电脑技术曾令我顶礼膜拜——也许现在他脱离技术工作多年,已经有所生疏了罢,但在当时,却是我在技术上极少敬佩的人之一。他是一个在技术上善于钻研而且悟性极高的人。我简直无法忘记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影响我走上网站开发这条道路的。我简直无法忘记他向我演示他刚刚学会的ASP程序的情景。我清楚地记得他在那个网名叫“白衣”的激光研究所网站管理员那里申请到的一个空间,把自己做的一个小留言本程序放在上面。那简直让我羡慕到彻夜难眠。也正是在他的指导下,我忐忑地给“白衣”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委婉而诚恳地表示要申请一个空间来学习ASP,后来便有了我的第一个ASP网站。我的网站开发之路正式起航。此后我们并肩战斗,做这样那样的网站。最清楚的一次是我们一起给生命科学学院建了一个站,我还保留了当时的一张照片,虽然只是个背影。
再后来,我拓荒式地转向了PHP,继续前行。二鬼子似乎要考研,这真是个笑话。起码当时在我看来,他是考不上的。要知道我们同样都是为学习自己喜欢的技术而几乎放弃学业的人——我大学里六次高数只有一次及格,最低的时候只有7分,而他并不比我强多少。这样一个人要去考研,无异天方夜谭。但他执拗地学起来了。也许学了半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考研的时候,他几乎创造了奇迹——他虽然没有考上,但几乎考上了,而且数学并没有受限。这已经是一个奇迹。我更加相信他是一个聪明人,他只是需要再多一点时间。
二鬼子是一个十分幽默的人。这样的人总是让人感到亲近。我喜欢那种既理性又不乏多情,既严谨又会偶尔放纵,既谦谦君子而又偶尔癫狂不羁,既温文尔雅而又不失粗犷豪放,既有原则而又宽容的人。我们会为一个技术问题而穷追不舍彻夜不休,也会在人生得意失意处举杯痛饮醉眠芳草。不过二鬼子的酒量小得惊人,他曾经因为喝了一瓶啤酒而倒地不醒发生短暂性失忆。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个充满豪气的性情中人。我自认为也是一个幽默的人,和他在一起,我简直在享受语言的快乐。和他在一起,我们可以享受夸张的快乐、讽刺的快乐甚至骂人和被骂的快乐。他的语言天赋惊人。
整个大学里二鬼子都没有谈女朋友,我甚至认为他连这样的梦都没做过。这样的人并不多。首先我想这个绰号影响了他。女生们当中都知道他叫二鬼子,又加上外貌的原因,再加上穷的原因——每个经历过贫穷的人都知道贫穷会使人自卑。爱情是一件多么需要炫耀自己的事情啊。一个贫穷的人可以炫耀的事情实在不多,于是爱情变成了不可企及的奢侈品。我确信四年里他没有追过哪个女生,也没有哪个女生追过他。如果有,也是发生在心里面。反正我没有见过他约会。
毕业的时候,二鬼子的运气还不错,去了一个事业单位。工作以后我去过一次,他设宴招待,人已然胖了许多,白净了许多,胡子刮的干干净净,衣服也整齐了。我去了他的宿舍,一个拥挤到让人窒息的地方。再后来听说他买房了,虽然只是很小的一居室。再后来听说找了女朋友,听说还是个护士,听说长得还挺漂亮。再后来他结婚了——2008年12月他结婚了,而我当时在北京,未能亲自赶去,这一直让我心怀愧疚。再后来他有了孩子,而且是个儿子。上次见他还是2年前,我很想再见见他,以及他的儿子。我也一直想见见他的老婆,是否真的挺漂亮。他曾经是多么不堪的一个人啊,怎么配有一个漂亮的老婆?然而他似乎就有这个福气。他又一次运气不错。
最近听说他不太如意,主要是经济上的。缺钱的日子我从不陌生,所以我能体会他的处境。我们这一代从一穷二白的农村家庭打拼到城市里来的人,处境大都没什么两样。好在一直有信心在,有希望在。困难总会过去,就像过去的这些年中被我们一一化解的那无数困难一样。
二鬼子有个博客,更新的频率比地震还低。地震一年好几次,他的博客却经年不变。他很少写些文艺方面的文章,但我知道他有这个才华。今天看到他这首小诗,“偶尔谈笑间,一丝过往乍现。”。我想起了那些过往的事,于是忍不住写下这些。
2010年4月20日深夜
春天来了。虽然还不时有个冷天,但春天毕竟来了。路边的树木,楼下的花草,都开始萌芽了。我最近一直在打算,在阳台上辟出一块小地方,填上土,种点植物,比如葫芦或者蔬菜都可以。不过筹划了半个多月,至今没有实施。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砖头。我估算了一下,大约需要30块砖就能实现我的蓝图,不过在城市里买砖可不容易,不知道哪里有卖,即使有,运输也是个问题,就这么搁置下了。有人曾建议晚上去路边施工的地方偷一些,我也想过这个办法,上班的路上很多施工的工地,砖头是不少的。不过想来想去觉得为了这三十块砖,倘若被人捉住,落个小偷的罪名,实在不值。
楚涵回家了。清明节的时候,母亲要回家看看,于是便回去了。我也有快一年没回家了,本打算同回,后来因为好友L君结婚,请我去帮忙,因此未能成行。母亲把楚涵抱回去了,于是我们又恢复了两口之家。楚涵在家的时候,大人也被拴在家里,有时觉得孩子是个负担,是个累赘。现在又变成两个人了,却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自由,反而觉得生活索然无味。晚上LP只能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电视,我坐在电脑前上网,一晚上可能都没句话。LP说,楚涵不在家,家里不热闹了。这何尝不也是我的感受。没有孩子的时候,觉得单身自由。有了孩子,虽然时间上有些羁绊,不能随心所欲,但也能获得单身时不能获得的天伦之乐。我们都很想念她,隔两天就要打一个电话。只可惜楚涵还不会说话,听不懂爸爸妈妈的牵挂。
最近很忙。不是一般的忙。最近两周好几个项目挤到了一块,频繁熬夜加班,劳累不堪。在电脑前面坐久了,腰酸背疼,连胳膊都疼,眼睛更不用说,酸痛,干涩,困。昨天凌晨2点时才睡下,4点半起床去L君那里帮忙。最近的一周多,每天24小时我大概平均只能睡个零头。前一段时间靠舒适的生活和每周打两小时篮球积攒起来的好状态,这两周消耗殆尽。现在身体疲惫慵懒。当然,博客也是鲜有更新。
还有一些事。比如笔记本又烧了显卡,这已经是半年来的第四次,又拿去科技市场修理。相机的液晶屏坏了半年多了,因维修费用较高,一直没有舍得修。前几天咬咬牙,一并修了。可惜楚涵不在家,否则又可以拍几张照片传上来了。
我一直喜欢春天。这是一个让人感受到生机的季节。平淡的生活有时寂静到可怕,沉闷到可怕,僵硬到可怕。而春天,可以让人起码在心情上时常融化开来。当我看到那些花花草草长出嫩芽的时候,立即想到了一个字“萌”。于是拿来做标题吧。
2010年4月11日午

在这个时常被虚伪包裹的国度
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动到流泪
在这个生命时常被漠视的地方
我经很久没有期待奇迹
在这个矿难多到让人麻木的地方
我已经很久保持沉默
三月二十八日 王家岭
当灭顶之灾瞬间降临
一百五十三名兄弟
当死神紧紧扼住你们的咽喉
你们在微弱的喘息中坚持
你们在六百米的地下
一个何等的炼狱中坚持
奇迹!
奇迹!
我们和你们一样期待着奇迹
却又何曾真的相信过奇迹
八天八夜!
八天八夜!
我们在争分夺秒的抢险中度日如年
你们在亲人泣血的哭泣中度日如年
你们在黑暗的井洞中
在饥渴交迫中度日如年
你们在与死神搏斗
我们在与生命赛跑
八天八夜!
八天八夜!
当第一声呼喊传入巷道
当第一丝光线刺破阴暗
当我们看到你孱弱的身躯
仍在保持着取暖的姿势
当我们伸出手
感觉到你微弱的呼吸
当你被抬上担架
当第一副担架出现在井口
当明媚的阳光照又在你的身上
当你缓缓地扬起手挥向人群
人们不离不弃的坚持
和无尽的付出
顿时被赋予无上的意义
只为你无价的生命
终于重见天日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怎么会是这么晴朗的一天
老天应该被感动到流泪啊
一
四
九
二十四
四十二
五十五
七十七
……
数字在一个个增长
奇迹在一步步延续
不要停下!
不要停下!
我看到你一直紧攥的拳头
那是如铁的信念
坚强如斯的生命
我们和你在一起
坚持!
坚持!
奇迹已经发生
在最后的煎熬中
坚持期待吧
期待一个伟大的结局
这是从未有过的壮丽
四月五日
清明节
张家岭
这一天从此不再意味着故去
它创造了新生
这一天从此不再代表着忧伤
它带来了狂喜
我为你们热泪盈眶
就是你们
所有的你们
2010年4月5日下午14点30分 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