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改了一个QQ签名,本是无意之举,不料却引来了一些围观。有的朋友问我,你这签名啥意思啊?有的朋友则说,你这签名太悲了,有些消极。还有朋友说,你这签名很吓人。不过没有一个人说这个签名很深刻——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这句话不是我的原创。这是鲁迅先生的散文集《野草》中的一篇《墓碣文》中的句子。我不记得何时看过这篇文章,也忘记了大部分词句,只是这一句话记忆深刻,昨天无意间想起了,便做了签名。我知道,如果我在后面加上“鲁迅”两个字,就一定有人会说这句话很深刻了——我简直做过这样的试验。我曾把自己写的句子念给别人听,说是某大作家写的,他们便连声称好,甚至能分析出一堆深刻的道理。或者我把一些名人的句子念给他们,说是我自己写的,他们则完全不屑一顾了。我知道了文学也是讲究出身的。就像这句话,倘若是我说的,便一文不值了,但它偏偏是鲁迅大师的手笔,也许是现在读鲁迅的人也确实少了罢,因此围观的人才这么多。
这是一篇十分怪异的文章。也是鲁迅先生的散文(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首散文诗)中公认的最难理解的篇章之一。在写这篇东西之前,我从百度搜到全文,念给LP听,问她怎么样,她想了一想,说:鲁迅写文章有时候也跟说梦话似的。说完便转身去看电视去了。电视里正在播新版《三国》,也许那个比这篇文章有意思得多。我本想指出她的肤浅,但转念之间,却发现她未必错了。鲁迅先生正是描写了一场梦境。文章的一开头便是“我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可不就是做了个梦吗?我惊喜地发现这也是对这篇文章的一种解释——当然这只有十万分之一的可能。我相信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必然是多梦的,而且他们的梦也一定是足够荒诞离奇的。所以这未必不是鲁迅先生在梦境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后的产物。当然在无数分析家、研究家的眼里,鲁迅先生这么伟大的文学家,不会去简单地记述一个梦境而不添加批判讽刺与忧国忧民在里面。
关于这篇短文的主旨,数十年来一直有人在研究,观点各不相同,有的观点甚至完全相反。我一直有一种观点,很多文学研究家们在研究古人的文章的时候跌入了历史的陷阱。他们更多地喜欢讨论历史而不是文学本身。我知道在欣赏某些文学作品的时候适当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作者个人处境是非常必要的,但很多研究家们的研究已经显然走火入魔,他们不认为文学可以明白如话,任何一篇文章如果没有三万字五万字的解读便是肤浅和错误的。他们忘记了“子非鱼”的典故。他们自以为了解历史,用记录在案的那一点点历史的碎片去试图还原作者的本意。他们更喜欢去抽丝剥茧般地、一厢情愿地、自以为是地分析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却不愿意去挖掘这些能够在成百上千年中感染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境遇下的人们的经典文字中的文学美感和某种普遍地代表性。他们一说起鲁迅便要把他的一切作品打上忧国忧民、针砭时弊与拯救民族的烙印,而不愿意去琢磨在国民党反动派早已经零落成尘的今天为什么还有人喜欢读这样的文字。一切不朽的作品必然具有穿越时空能力,它带给人们的共鸣可以持续千年,完全不受历史的局限。将文学欣赏人为复杂化,是这帮研究者最大的贡献。研究宏观的历史可为今人借鉴,微观的历史仅供学者谈资。而因文学欣赏而研究微观到作者写作的当天吃过什么饭拉过什么屎放过几个屁的历史,则完全是迂腐文人们为了标榜自己的深刻而发明的蒙汗药。让人晕晕乎乎然后情不自禁地说“有深度”就是他们的追求。
鲁迅是因为时人以及后人对其文章的喜爱和认同而成就其伟大。而并不是在评论家们的“深刻”解读中伟大起来的。这些自以为可以分析鲁迅作品并自封正确的人,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可以超过鲁迅。他们何以有信心可以把将近一百年前一位思想巨人在写作时的感情看穿呢?他们何以敢去做这样的尝试呢?今人读鲁迅之作品,若能学得文字技巧之运用一二,词句章回之组织一二,抑扬褒贬之轻重一二,文学良心之要义一二,天下兴亡之忧喜一二,再有文字之学之优美、犀利、酣畅与精准一二,足矣。倘能在先生的某段文字中察觉到某种共鸣,似诉心中无限事,那便是令人激动的意外之喜。除此之外,概无其他。至于先生写作时的来龙去脉如何,所思所想如何,所作所为如何,真的不必追究,也不可能追究。倘若非要把这种追问说成一种学问,顶多只能算是一种“好奇心”学问,自娱尚可,唬人就不对了。
我忽然又有一个重要发现,且看先生在这篇《墓碣文》中的另一句话: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不妨抛开这篇文章的整体,单就断章取义地把这一句话当成一个比喻。自己品尝自己的心,刚挖出来时,身体剧痛尝不出真正味道。而痛定之后慢慢品尝,心却已经陈旧,怎能尝出最初的味道。先生之心,自己不能得其味,更忧后人不能知其味。后人即便品尝一二,也是“陈旧”之心,岂是先生本味!自知无人可知其本味,先生释然曰:“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任由一个个不能“答我”的路人走过他的墓旁,他是在释然地微笑着的。
必须再次强调上面这段以及之前的“梦境”论并非我对这片《墓碣文》的全部理解,只是我在随手填补一个个十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不论是什么文章,对于读者而言都无需被限制在一个标准答案式的狭小的理解空间里。这也是我对语文教育中所谓“文学欣赏”题一直十分抵制的原因。记得某名人曾经说过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我们老祖宗也常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些原则对于文学欣赏尤其重要。倘若一篇文章只能有一个主旨,只能按一种方式去理解,只能在同一个点上产生共鸣,那无疑是可笑之极、荒唐至极直至悲哀至极的。这种做法是对教育的亵渎,对文化的犯罪。喜欢一篇文章,一万个人可以有一万个理由,哪一个理由才是“本味”?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可以有学派之分、主流与非主流之分、普遍与个别之分,但不应该有对错之分。科学的词典里没有“也许”,艺术的书本上没有“肯定”。所谓文学欣赏的标准答案,是对思想的禁锢,艺术的扼杀。
但求爽口,莫问本味。我感受到先生这篇文章的深邃,又感受到它散发着一种难以捉摸的神秘气息。这种气息吸引了我。也许只是那一句“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吸引了我,让我时时回味。我讲不出道道,也说不出历史,哪怕这篇文章不是出自鲁迅,哪怕出自一个无名小辈之手吧,也足以为我吸引。其他所有喜欢这篇文章的人未必都是像我一样的感受,让他们记住这篇文章的原因可能千差万别,这正是这篇文章的魅力所在,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先生的魅力所在。倘若一定要站出一个权威定出有一个本味,倘先生在世,料亦不能容。
不求本味并非不求甚解,本味非解,本味无解。
2010年5月12日深夜
附:《墓碣文》
我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读着上面的刻辞。
那墓碣似是沙石所制,剥落很多,又有苔藓丛生,仅存有限的文句——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
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离开!……
我绕到碣后,才见孤坟,上无草木,且已颓坏。即从大阙口中,窥见死尸,胸腹俱破,中无心肝。而脸上却绝不显哀乐之状,但蒙蒙如烟然。
我在疑惧中不及回身,然而已看见墓碣阴面的残存的文句——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
我就要离开。而死尸已在坟中坐起,口唇不动,然而说——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
鲁迅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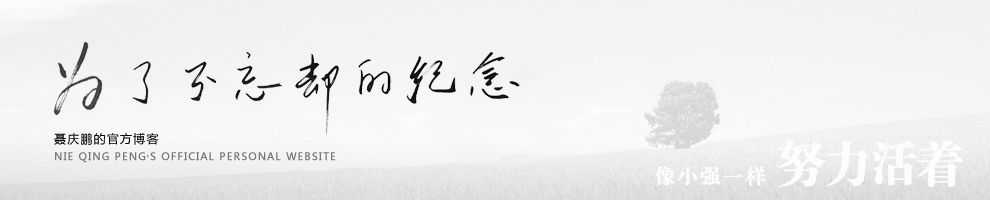

以前我看到一些画或者书法,觉得一般(当然,我只是外行人看热闹。)我在想也许我写成那样,别人不一定觉得那叫艺术吧。
果然还是讲出身的。
其实,以前的一些文人墨客写的文章或者诗词,也许并没有那么多意思。是不是我们现代人想多了,是那些所谓的学者给赋予的涵义呢。
就如《登幽州台歌》我找了很多翻译以及鉴赏,但是我觉得都不是那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