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我会时常想起一些人。想起他们的样子,或者是一副表情,或者是一片身影,也或者是一个动作。这些人都曾在我生命中的某段时光中出现,有时我是他们的陪衬,有时他们是我的陪衬,到现在,他们成了我记忆中的时光的陪衬。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我曾有很深的影响,各方面的都有,所以能够让我今天还记得。我之所以要特别提起这些人,是因为这些人曾经出现,现在消失,将来也不知道何时再会出现,或者永远不会再出现。我知道他们此时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里,在他们各自的生活圈子里,过着自己的日子。但对我来说,他们似乎是不存在的。他们似乎只曾在某段时光中存在,某段记忆中存在,而当时光逝去,记忆尘封,他们,也越来越不真实。我越去回忆他们,就越觉得恍惚,恍惚地认为自己的那些时光,都是一个长长的梦。
这些人,太多了。像无数的星星点 缀在我记忆的各个角落。我无法一一数清他们。只能循着最亮的那几颗,描绘他们的轮廓。
第一章
我第一个想起的人竟是他,LJ君,曲阜师范大学办公室秘书科科长,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了。我想他首先想起他的发型,其次是挺大的鼻子,再次是和蔼的笑容,再再次,竟然想起了他说话的声音。我确信即使是今天我一定还能听出他的声音,尽管我们分别即将满10年。我们的相处也不过是一年多,相处的关系是老师和学生。那是我勤工俭学的一段经历,在那座大楼,仿佛是十楼还是十一楼,东边的一个办公室,很大的房子,用密码才能开门,里面好几台电脑,可以上网——免费上网,10年前这是多么大的奢望。我在那里度过了很多不眠之夜。有时加班,有时值班,有时就是为了等老师们下班了,可以用电脑上网。我在那里还认识了另外几个勤工俭学的工友,大部分是中文系的,有一个LGY君,写得一手好文章。我甚至还记得他彻夜创作小说的情景,那小说叫做《一把好乳》,我知道光看这个名字,就是个有深度的小说。这扯得有点远了。我已经几乎记不起在LJ君的办公室时曾做了哪些有意义的工作,最多的大概就是给老师们安装操作系统,Windows98。记不清安装了多少,大概很多很多。我记得LJ君喜欢打乒乓球,办公室里常备球衣和球鞋,他经常在下午的时候在办公室换衣服打球。他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我至今也没觉得他很威严或者可怕,他对我们总是十分和蔼,就像大哥。我现在想,我那时是多么多么土,多么多么潦倒,多么多么幼稚甚至多么可怜的孩子呢?但他对我们很好,总是想到我们的困难。2003年8月我离开曲阜,他早早给我结清了勤工俭学的工钱,甚至还多申请了一些加班费。我还记起了他的老婆,一个瘦瘦的同样文静和蔼的女子,我还记得她的硕士论文的题目,叫做《乌鸦吉凶考辨》。在我离开曲阜后的不久,我就听说LJ君去北京了,似乎进了一家企业。无论是为了爱情还是事业,这都是一个让人钦佩的决定。也就是从那之后,我们再未联系。我知道如果我努力去找,总能联系到他的,但我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是不想他。但我并没有决心去联系他。联系了他,我能说些什么呢?就让他成为一个过客吗?起码目前,是这样的。
与LJ君同时想起的是同一办公室的WH君,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长者。他个子不高,戴个眼镜,喜欢穿风衣,整日西装革履,斯文得很,儒雅得很,十足的知识分子形象。我曾对他说,觉得他像郭沫若,他一笑置之。实际上我那时根本不了解郭沫若,大概只是曾经在书上见过郭沫若的肖像,那种戴着眼镜西装革履的形象,颇文学,也颇文艺,是我心目中最早的有学问且高风亮节学者的模型,于是便这么脱口而出了。后来我知道了说他像郭沫若未必是一种褒义,但我当时绝对是以无比崇敬的心情说的。他曾赠我一本签名的书《美德论》,至今还躺在我的书架里。我承认我没有认真读过那本书,但我却十分乐于珍惜和保管。在我十年多来的颠沛流离中,丢弃了很多东西也没有丢掉它。那时的WH君大概是比LJ君更大一些的领导,所以并不直接和我们这些学生有多少工作上的交流,更多的是私人的,生活里的。他曾多次和LJ君请我们学生吃饭,对于我那时候的见识来说,我跟着他们吃过一些那时看来足以回老家炫耀很久的饭局,吃了很多今天看来稀松平常但那是我叫不出名字的菜。哪怕是在学校东门吃过的几次馄饨,都是我大学里少有的改善伙食的机会,更分外觉得难忘。我知道他虽然没有像老师一样直接教过我什么,却深刻影响过我,以至于我都在并不近视的情况下勉强配了一副眼镜,并也喜欢穿西装和风衣。我今天仍能清楚地记起他的样子。现在想来,他那时是个很大的官,但当时不觉得,就是一个亲切的长者。后来听说他又做了更大的官,再后来,便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我知道如果我主动去找,曲阜还在那里,学校还在那里,他应该也还在那里。但我没有去联系过。我不知道我为何是这样一种人,怀念着他们,却还保持着距离,甚至害怕联系。我真心希望他现在过得好。我忽然很想再看一眼他的笑容,让人感到温暖和安详的笑容。
我还要必须想起一个人。LYT君,计算机系的书记。我不知道对于内心尊敬的长者用“君”称呼是否合适,但不小心习惯了。这是一个让人感觉充满能量,而且是正能量的长者。我与他之间主要通过三件事留下印像。一件是《弄潮》的创刊。大一的时候计算机系与数学系是一个系,大二的时候分成两个,也就是那时候他来到了计算机系。新系创建,一切都是新的,人人似乎都充满了干劲。计算机系决定创办一个系刊,我也忘记了怎么成为参与这个刊物创刊的一分子了,也许是大一的时候残梦未醒喜欢卖弄文字的缘故,在计算机这样的理科系,仿佛成了有点文采的人,于是有幸参与了这件事。那时候系里有很多充满激情的年轻人,LBW,WCX,对,都是多么好的年轻人,我今天想起来,都还有些庆幸,曾有他们一起共度大学时光。我们一起怀揣着梦想创办刊物,LYT君,或者说老书记,也是我们当中的激情一员。我那时不知道书记是个什么官,也没觉得是多大个官,我就把他当作一位尊敬的师长,与他时常有讨论甚至争论,而他就像博学且慈祥的父亲,总能给我们以最大的帮助。他给我们的刊物起了名字,弄潮,还题写了刊名。我清晰地记得我用我那台IBM 超级老爷机和刚刚自学的PS软件设计《弄潮》创刊号封面的情景。那个封面,两只跳跃出水面的海豚,在落日余晖下的剪影,美不胜收。我们曾在上面投入大量精力,征稿、审稿、编辑。我不记得这个刊物一共出了几期我便离开了,也不知道这个刊物现在是否还在——我想大概肯定已经不在了。
第二件事是辩论赛。也许是2002年,学校组织辩论赛,计算机系成立了一个队伍,LYT君是指导老师,队员是我,ZJY,LBW,MC(女),还有一个胖乎乎的女同学,请原谅我暂时想不起他的名字。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它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让我学会思考,甚至让我重新认识自己。我甚至怀疑我今天仍然带有的那种所谓“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否是那时的遗留。我们第一个对手是化学系,辩论的题目是“高薪养廉“,一个很有深度的话题,很适合对社会问题怀有激进看法的青年。我们于是经常到LYT君的办公室去,听他给我们分析问题,解释观点,我那时第一次感到和有思想深度的人对话是多么愉快,多么让人如饥似渴。他总是让我们说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很严肃的讨论。他要求我们必须要有独立的思考,他那句名言”脖子上要扛着自己的脑袋“,成为我多年的座右铭。第一轮辩论,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忘记了是否曾有隆重的庆贺,但紧随其后的惨败,才让我们收获更大。第二轮我们遇上了中文系,辩论的题目是”班门弄斧“。真应了这个题目,和中文系比口才,我们虽早有失败的准备,但未想到如此惨痛,尤其对我个人的表现来说。那时没有录像,如果有,我想我是不忍回看的。那时的他,就坐在台下。对于失败,他没有批评,甚至没有流露出失望,反而给我们以鼓励和表扬。那是将曾有些年轻气盛的我打回原形的一场比赛,也许从那之后,我开始尝试收敛。
第三件事,我甚至不想提起。但我知道人生不可能都是顺境,也不可能都是一路向前、向上,也有走弯路的时候,也有犯错误的时候,也有灰暗和不堪回首的时候。我感觉我能说出这件事,已经是巨大的勇气。而这勇气,也是LYT君灌输给我的,敢于直面自己错误的勇气。那是一次考试,临近毕业的一次大家看来无关紧要的考试,而且按照通行的潜规则,是一次走过场的考试。而就在这种思想的松懈中,一向特立独行,宁愿不及格也从不想歪门邪道的我,竟也打起了小抄。那位我虽然不能算怀恨,但至今仍无法释怀的Z老师,出乎所有人意料地严肃起来,一下抓出五六个人。对,作弊,一个对学生来说十分羞耻的词语。对于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说,这样一次错误足以毁掉一生的前途。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走投无路的我们一起去找他,LYT书记。包括我上面提到的辩论赛的队友ZJY君。在他的办公室,他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怎么有脸来找我!然后是可怕的沉寂,然后是女生先开始抽泣,然后是我们。而当我们抬起头时,看到他,LYT书记,紧咬着嘴唇,眼睛通红,也流下泪来。我感到我们真的刺痛了他,我们更哭地像个雨人。我第一次感到他真的生气,我从未见到他如此严厉,他真的生气了,当然更多的是痛心了。之后是一番长长的对话,桀骜不驯的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到毕业的时候,我们没有领到处分。我知道也许是他帮了我们,也许他没有。但不论有没有,在这件事上他带给我的,已经超过了这个有或没有的处分。
离校之前,我去过一次他办公室,我知道他喜欢收藏电话卡,便将一本我女朋友收集的电话卡送给他,并在后面附上一首小诗。他欣然接受了,看到诗的时候,他认真地念了,并问“怎么能说’再见无期’呢?毕业了也随时可以再见嘛。“。我说,不是说再也不见了,而是说再见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他一笑。从那以后,9年了,我真的,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不确定是否还能见他一次。我甚至有点羞于去见他。他大概退休了吧,他身体还好吗?我自认为是他曾很喜欢的学生,但9年了,自感没有做出令自己满意,以及令他引以为豪的成绩。我无法再捧一本电话卡去见他,而我又两手空空,我似乎没脸去见他,我不确定他是否还能记得我,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虽然他存在于我生命里的两年多,从时间上只是一个匆匆而过的人。
2013年4月10日 深夜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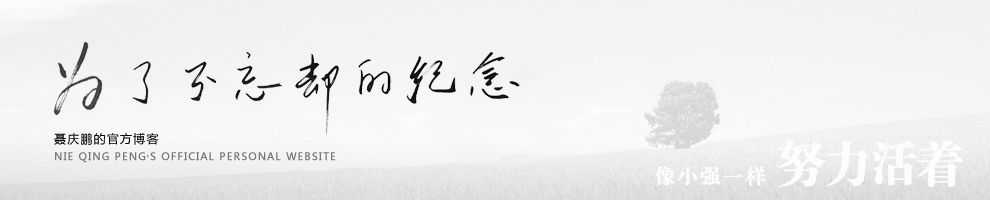
 已有3人评论
已有3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