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之中国男子及二十岁,始戴帽子,施行冠礼。因此在所谓“弱冠”一词中,有着年少、学习、追求生之意义——等等意味。
然后作为成人,一生探索真理之道。诸如忠孝节义以及报国之志,都受教于从家至国,并渐渐成为被称为士子的、知识人的日常意识。
一部中国史,可以说,就是由这种忠烈、仁义、多才等类型的名士装点而成。如仅仅一介农夫就立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诸葛孔明。如向后世呼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生存方式的范仲淹。更如听说帝尧要禅位于己、就以为污脏以至于洗耳河畔的许由。都已传为美谈、但却是久远的逝事了。
其中最为完璧者,或许当称哀国之亡、流浪故乡大地之末,自沉于河的屈原了。由于难忘的殉国行为,留存的诗被代代传诵。楚辞即它的文学应该说是中国文化辉煌的极顶。徘徊于洞庭波打之岸,吟咏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的形象,衍变成了中国的求道知识人的象征。
但是,尽管绵绵两千年赞美屈原不已,选择屈原之道的例子,却意外地少而又少。屈原的文言诗句,渐渐变得难懂。取而代之,从市井到农村,无人不知的句子,已经是孔子的“学而优则仕”。流行中国的观点,已经是先读书然后做治人之官。
这样,屈原变成了非文人难懂的古典。在必须实干的时候,中国知识人大致都是选择了升官之道——也就是仕途。
对于“道”的言与行,就这样分离了。
应当说现代也没有什么两样。
若研究原因,首先应指出对于权力的恐怖。比如,从今天知识阶层对“文化大革命”的诅咒式态度中,就能看到一种绝对不允许“四人帮”极“左”时代重现的、认真的责任感。
被体制和权利强加于身的恐怖,或者会使人们为体制与权利效力。
其次,所谓之穷,也是个非常能改变人的东西。远在懂了人口问题的今日以前许久,此国之人就知道:只有极少数人才能饱足;活的得意的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极少数——这种认识,在人们的意识中盘根错节,被坚信至今。
甘肃省有个黄土高原包围的农村小县。几乎连年,大学入学率在全省名列前茅。中学生之志,就是离家远走。哪怕自己一人从黄土中解脱,也会使双亲安慰。
中国古语中,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词,毛泽东曾使用此语,解释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毛”与“皮”的关系。
毛,已经绝望与对故乡严峻贫穷的斗争,已不愿意在僻远的乡里耗尽人生。想逃离皮。想背叛皮并扔了它。
从来都只是若干人才能登高官财主之位;其余者则永远穷苦、无权、收辱、被压迫、成为牺牲。残酷的历史,一直在如此教育着。毛,已经不再相信屈原的诗了。
今天也一样。不可能全国全民族十二亿人,全都变成有钱阔人。道路,就像扔在那儿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不快点迈出脚去,他就要落入别人之手。路上已经很挤。美国式的生活,人人都在瞄着。只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把那富裕弄到手。
对政治的恐怖,对个人富足的追求,改造了中国知识人命运。——向权力妥协!——嘴上虽不说,这是心底的结论。只要有了权力的支撑,何止美国式的小汽车小洋房,——包括在体制容忍范围内的对权力的批判,都是可能的。
古典之道,已经被逼向终结。再言及屈原其诗其行的人,不仅仅要被女人嘲笑为迂怪,更会被视为危险的说谎者,为社会所孤立。毛,脱落者飘散着,从皮上分离不已。那头被叫做“祖国”或者“文化”的牛,正一天天消瘦和丑陋。
这本小书,就是在这一世纪之末,基于著者被时代大潮胁裹、得各地体验的一本——为自己一毛而求其皮的心事录。被人说成国家主义者也罢,被人说成原教旨主义者也罢,与我都无所谓。思想正在疼痛之中。虽然没有援助那牛的能力和勇气,但是,望着那牛流淌的眼泪,我要写下——这传遍周身的战栗。
张承志
1999年春,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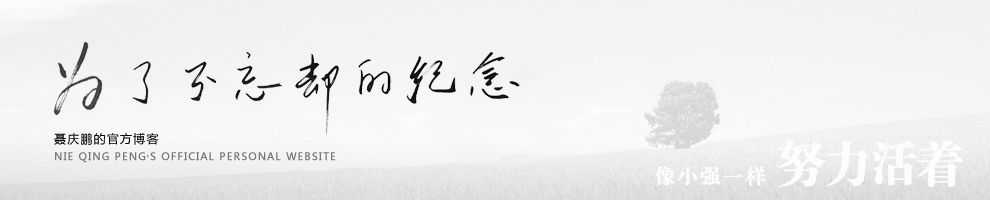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