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奶奶去世三周年。按风俗,亲友们要聚到一起,搞一次大的纪念活动,也就是上坟。这个活动是无论如何要参加的。而且正好赶到了两门课上完之后的休息期,省了请假的麻烦。于是提前一天于8月11日赶回老家。
17年前爷爷去世的时候,正是那一年冬天里最冷的一天,大雪纷飞,积雪没膝。而三年前奶奶的去世,却赶上05年夏天里最热的一天。那天早上母亲给我打来电话,说奶奶病危,让我赶回去。我已经料到事情不妙。刚赶到汽车站尚未登车,电话又打过来,奶奶已经辞世。我强忍住没有让眼泪流出。回到家,直奔老宅,进到堂屋,棺椁已经摆在了屋中央。亲友族众跪拥四周。大概是担心天气过热,棺材盖没有完全盖上,留了一道缝隙,用一台电风扇吹风。我通过这个缝隙看了奶奶最后一面。眼泪再也无法抑制,我哭伏于地。
再以后,就是按照风俗发丧。在村子后面的山上,爷爷的坟旁边,早已差人挖好了合葬的墓坑。棺椁被抬到一辆板车上,摇摇晃晃向着山上进发。我拉不动这板车,我在后面推着。家里的长辈说我可以不用去,但我一定要去的。哪怕只是扶着,哪怕只是跟在后面,我也要送她老人家这一程,这是我仅剩的唯一机会。那天的烈日似乎要晒干一切,板车吱吱呀呀沿着崎岖的山路爬行。我在后面奋力的往前推,用尽全身的力气。汗如雨下。我不想去擦汗,我想用它掩盖流下的泪水。我希望这路长一些,再长一些,让我一直这样推下去。我长到二十三岁都没有想起曾经为奶奶做过什么,现在她去了,这是我唯一可以为她做的。
时间过得一如既往地快。奶奶埋在那个土丘下面已经三年了。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我和她最后一次的交谈,那是05年7月的一个清晨,我从老家返回日照,路过她的宅子,进去跟她告别。她坐在堂屋门口的方凳上,靠着门框,形容憔悴。看到我进来,她的第一句话就是:“鹏,咱娘俩见一面少一面了。”。我知道她的冠心病很严重,但没想到这么快。仅仅是一个多月以后,她就去了。而这句话,也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再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躺在那个闷热的大木头盒子中。八十三岁的她寿终正寝。
奶奶的一辈子经历了太多磨难,虽然从外表看来她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村老太太。我知道她的很多故事,这些故事感动着我,以至于每每想起时都有流泪的冲动。在我心中她一直是一个伟人。这一点毫不夸张。可能她们这一辈人很多都和她有相似的经历。这是不平凡的一辈人,是伟大的一辈人。她们所经历和承受的,是中国五千年历史和新中国五十年历史的缩影的叠加。她们的一生,是一部部传奇。
奶奶养育了四子二女,还有5个孙子和5个孙女。在四个儿子中她最担心我父亲,因为他日子过得最穷。孙子孙女中,她最担心我,怕我没钱上学。从我考上高中她就开始担心我没有学费。后来又考上大学,情况更加糟糕。她自己是没有什么钱的,不过每次寒暑假回家,她都能给我五十块钱。我从曲阜给她买了一副带有孔子画像的挂历,她高高地挂在堂屋里,直到现在,空荡荡的屋子里那副挂历仍然在,布满了蜘蛛网。后来在助学贷款的帮助下我的学业终于得以完成,我也找到了一份工作,家境终于要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不过这时候她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已经不足以让她再关心我在日照干什么样的工作。她对于我能够完成学业已经非常满意。她还有另外一个心愿,就是能够看到我结婚,但是她终于没有等到,这是我欠她的。
三年了,奶奶的坟头已经长满了荒草。甚至还长出了一棵小树。她和她的全部故事都被埋在了这个土丘之中。春去秋来,她的故事会越来越少的被提起,她将从子孙后代的记忆中一代代淡化,直到没人知道她的名字。但起码在今天,她留给我的印象还是如此鲜活,她的音容笑貌还是如此清晰,我不能也无法假装忘记。我必须向她表达些什么,这些东西在过去的三年中早就应该表达的。
她不识字。甚至连数字都不认识。我试图用这些文字表达思念或者牵挂,但她是看不懂的。上坟的时候我在她的坟前烧了一堆纸钱,然后磕了三个头。我想这样的形式她能读懂。
2008年8月30日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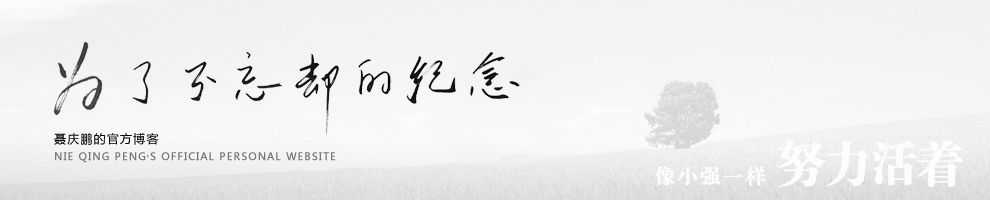

哈哈,有空来中南还吃饭,我请你!
#jingya# TO: 胡锦涛
您这个评论俺都不敢留,让网警看到了还了得,您可别开这样的玩笑。
#yumen#逝者安息,生者奋发!老奶奶地下有知看到你今天的成就会感到很欣慰的。 #xiyue#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