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一个铺满青草的土坡
坡顶站着一棵茂密的樱花树
树下躺着一块大石头
石头上坐着我的妻和女儿
女儿在吃着糖葫芦
秋日的阳光
正穿过湛蓝的天空
我攀登着
向着她们
她们笑眯眯地望着我
这一刹那——
分明曾在哪里见过
是心里
梦里
还是童话里
这一刻
在我眼睛里
2012年9月23日 日照植物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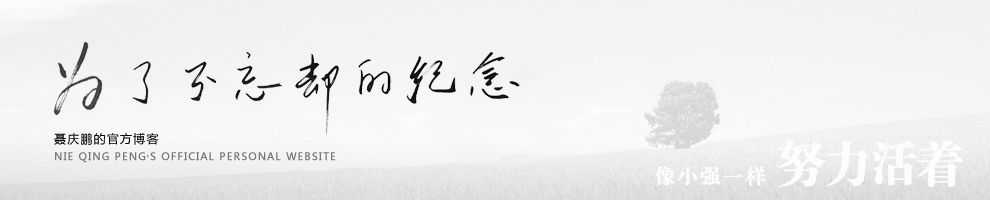
我看见一个铺满青草的土坡
坡顶站着一棵茂密的樱花树
树下躺着一块大石头
石头上坐着我的妻和女儿
女儿在吃着糖葫芦
秋日的阳光
正穿过湛蓝的天空
我攀登着
向着她们
她们笑眯眯地望着我
这一刹那——
分明曾在哪里见过
是心里
梦里
还是童话里
这一刻
在我眼睛里
2012年9月23日 日照植物园
 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 我忽然想起我的第一台电脑
那机箱里散发出的热气
都带着电子元件的香味
自从我有了很多台电脑
我对电脑就没了感情
它从一件爱不释手的玩具
变成了一件冰冷的工具
就像我喜欢上的第一个女人
自从我喜欢上好几个女人
我就弄丢了我的爱情
它从一种美妙醉人的情感
变成了一种赤裸的欲望
2012.9.8薄暮

作为一个中国人,而且是山东人,如果说没有听说过泰山,是不可能的。听说过之后如果从来没有心向往之,也是不可能的。泰山蜚声海内外,威名震古今,似乎快要成为中华精神的一个化身了。“五岳独尊”,拥有这样一个名头的山,足以让人不光有登高一望、俯仰天地的向往,更有心灵朝圣的意味。
中国人似乎一直以来对爬山情有独钟。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才子佳人们虽然都是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但却似乎偏爱体力消耗很大的登山。登山就像饮酒一样能够为才子们发挥才情注入兴奋剂。李白就是个典型,一生留下无数与山有关的诗作。那句儿时便十分熟悉且向往的“万里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深深的影响着我。还有那句“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更是恍然若仙。李白做梦都在爬山,那首美妙绝伦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证明。好多名山大川之所以成名,很多也是因为有了这些名人曾经的驻足。以至于如今很多山上都诞生了一些所谓“某某登临处”这样的景点。当然他们去时究竟在何处驻足可能没那么确定,但去过是确定的, 有诗作为证,有碑记为证,有“留言”为证。
泰山就是这样的一座山。从山下一直到顶峰,巨石、崖壁之上到处都刻满了历朝历代的游人留下的感悟。大多是对泰山景色的赞叹,也有对人生的思考。这里面不乏孔子这样的至圣先师,杜甫这样的人民艺术家,还有皇帝老子、名臣良将、社会贤达各色人等。我知道石刻是门很高的手艺,除了一些粗糙的“某某到此一游”之外,其他的定然不是自己带了家伙边走边写边刻上去的,大概有的留下墨宝,有的留下文章,后人求得然后找人刻上去的。总之,这些石刻体现着雕刻的魅力、汉语的魅力、书法的魅力、文化的魅力和作者的个人魅力,进而升华为整个泰山的人文魅力。每一方石刻、每一通古碑背后都蕴藏着一个故事,这些故事或婉约或壮烈,或曲折离奇或引人入胜,透过这些故事我们知道了这里曾有些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这是非常有趣的事。对于一座名山而言,高崖、深涧、奇峰、险路、巨木、古寺是基本构成要件,在旅游过度开发的今日,俯拾即是,难言特色。而历史、古迹和人文气息是一座山本质的沉淀,是最令人向往和回味的地方,也是一座山独有的灵魂。
我不知道自己何时知道泰山,但对泰山的仰慕在过去三十年接触的电视、电影、书本和人们的口口相传中不断得到强化。无论是否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只有去了,才能死心。我之前距离泰山最近的一次是2007年,我去泰安的山东科技大学参加工程硕士考试。当时住的地点就在泰山脚下,但时间关系,未能前往,只是在路边一个小店里买了一块不知道真假的“泰山石敢当”。再早一些的时候,我在曲阜求学,那是一个离泰安很近的地方,但不知道是决心不足还是机缘未到,到大学毕业也未能前往。工作后来到了日照,距离泰山又远了一些,但登泰山的梦似乎并不曾远去,只是一直缺乏一个斩钉截铁的理由。很多时候我们距离做成一件事只需要一个决心。当我们决定放弃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就能找到理由,而要做成一件事情却显得格外困难。就像这次泰山之旅,险些在天气炎热、花钱等理由中流产。而正是靠着心血来潮的冲动,才将这些理由抛之脑后,最终得以成行。
8月4日中午出发,绕道沂南接上姐姐和姐夫,把楚涵寄到老家,经蒙阴到达泰安的时候是下午5点多。天公作美,台风“达维”余威犹在,沿线都是阴天,泰安有点毛毛雨,气温为近日最低,适宜登山。6日一早,在宾馆吃了早饭,驱车到了天外村。按照之前制定的计划,为了照顾两个女人的体力,打算从天外村乘车到中天门。不料刚到天外村,有人上来询问,表示可以带车上山,比坐大巴上山划算。4个人往返中天门车费要240,而把车带到中天门只要100。显然这是一个便宜。于是当即答应。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被骗子骗到都是因为贪小便宜——这个道理搁在平时谁都懂,但骗子的本事就在于让你感觉这真的是一个便宜而不是骗局。那人指引着我们的车钻入一条坎坷不平的山路,走到一个村子里,便说中天门不远了,你们从这里上去吧。付了100元“导游费”,买了票,从小路进了山,遇到路人,问之中天门多远,答曰还有4公里。4公里听起来不远,但已经隐隐有了些上当的感觉。走了不远便到了一个叫“斗母宫”的地方,在路边买了一份地图,原来我们登山的位置就是泰山正门红门往西不远的地方——几乎是从红门爬上来的。很显然,这100被骗了。好在被骗不多,而且无论如何确实进了山,爬山的兴致还是压过了被骗的怒火,不能因此扫了兴致,还是专心爬山吧。
比之于其他我爬过的山,泰山的路要宽一些,比较好走。从斗母宫到中天门这一段,海拔落差不大,相对比较平坦。沿途有革命烈士纪念碑、总理奉安纪念碑、壶天阁、回马岭、四槐树等一些景点。初步登山,大家兴致都很高,体力也充沛,再加上日未出,雾未散,天气稍阴,凉风习习,边走边观赏风景,拍照片,十分惬意。路上见到了著名的“风月无边”石刻,不过这两个字比想象中的小的多,不甚壮观。倒是有块“青未了”的石刻,让人感觉颇有意境,便照了一张相。山路右边有山涧,流水淙淙,装了一瓶,饮之味甘,清冽爽口。山路每行不远便会有一处景点、凉亭或者高台,供人驻足休憩。边上往往有小商铺,主要卖些旅游纪念品,水和黄瓜、西瓜之类的水果,物价虽数倍于山下,但毕竟靠挑山工肩挑背扛,着实不易。
9点半到了中天门,气象豁然开朗起来。远处的高峰从树木的缝隙中显现出来,壁立千尺,蔚为壮观。比之顶峰,中天门不过一土丘而已。这时太阳也出来了,没有树荫的地方已经有些炎热。两个女人的体力,已然没有信心继续爬下一段,便送她们去坐缆车,并负责行李。我和姐夫拿一个相机,一人一瓶水,继续向南天门进发。
中天门到南天门才是真正挑战耐力的一段。10点左右从中天门汽车站出发,上行不远,到了一处“迎天”牌坊,看这名字,便是要起步登天了。再前行不远,遇一石刻群,有“峻岭”“曲径通霄”“人间天上”等石刻若干。再行一段,便到了云步桥,一座民国修建的石桥。过了云步桥,山路陡然,平地渐少,石阶渐高。此时人已气喘如牛,每五六十阶便要休息一次。恰好遇到卖登山杖的妇女,买了两根,一人一根,拄杖前行。这一路石刻很多,发现其中一方以古隶写道:“愿同胞努力前进,上达极峰,独立南天门,高瞻远瞩,捧日拏云……民国十八年九月三十日醴陵袁家普识”。虽然不知道这袁家普为何人,但这句话还是鼓舞了我,咬紧牙关,戮力前行。回来后查了百科,才知道袁家普乃民国名士,为官为学皆颇有风骨,登此山时已65岁,不禁更加敬佩几分。过了五大夫松、飞来石、东岳庙、望人松、万丈碑,到了一处石刻集中之地。有隆庆五年山东按察使吴文叶所书“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八个大字,康熙年泰安使者祁国祚题“举步腾云”。还有道光年王鸿题的小诗一首“梦游天地外,身堕烟霞中。愿举饱腹稿,万古开心胸。”,豪气干云,颇壮气势。再往上爬,便赫然到了十八盘。之前只是听说,真正到了这里,还是有几分怯意,1600级石阶,海拔落差400米,登泰山的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段。和姐夫在十八盘指示牌前照了相,略作休整之后,开始挑战。这一段不免气喘如雷,汗流如雨,每二三十阶便要休息。此时休息也顾不得干净,石阶上随处一坐便可喘息。一路上不时见有老者、妇女和十来岁的孩子,这也增加了自己的信心。他们能上去,咱也能上去!怀着这样的信念,咬紧牙关,一路石阶而上,过了龙门,登了升仙坊,南天门终于远远在望。回望来路,山路曲折,绵延无尽,山高路陡,人微如蚁。这时体力已经透支,每上一阶,肌肉酸软。我想起了李白在《蜀道难》中的嗟叹“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感受是一样的,只不过他“坐长叹”,我是“坐长喘”。
到达南天门的时候,两个女人已经等候多时。难怪,已经是正午12点了。可惜的是袁家普说的“独立南天门”无法实现,游人如织,摩肩接踵,别说独立,就是找个能照相的地方都极难。而且此处台阶极陡,不宜久留。最关键的是现在已经举步维艰,饥饿难忍。早上的一桶大碗面,早已消耗得干干净净,急需补充能量。于是过了南天门,到了天街,找了一处人少的地方,拿出东西,饱餐一顿。休整完毕之后,一起向玉皇顶进发。沿途欣赏了天街、孔子庙、西神门、日观峰、青帝宫等景点,最后终于抵达了泰山顶峰的标志性石刻“五岳独尊”前。这块石头没有电视中和图片上见的那么壮观,只有2米多高。但经历了6个多小时精疲力尽的攀登,终于见到这四个字,还是分外激动的。可惜的是人太多,想照一张漂亮的照片困难得很,勉强照了一张,回来后发现少了一个“五”,算是小小的遗憾吧。从五岳独尊石南行数步,有一处崖壁。这时候天气放晴,云雾散尽,山在云上,人在云端,天空湛蓝,白云如棉,俯视泰安城,尽收眼底。据说在晚上从这里还能看到济南的灯光。站在山巅,让人感叹山河壮美,自然神奇。凡尘琐事抛诸脑后,来路辛苦化为云烟,游目骋怀,心旷神怡。
游玩到2点多,考虑到还要返程,便乘坐索道下山。不料索道人满为患,队伍排了数里,烈日下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终于在3点多坐上缆车。十分钟不到,下到中天门。老姐体力已然极限,寸步难移,只好乘车下山。我们三人自觉尚可,便从中山门步行去开车。下山毕竟比上山快些,而且路上已然兴致全无,一心只想天黑前返程,用了一个半小时,休息了四五次,便到了山底。驱车去天外村车站接上老姐,在路边吃了一个西瓜,7点开始返程。9点抵达沂南,父亲已经炖好了鸡汤,孩子已经入睡。晚上10点钟从沂南启程,12点返回日照,泰山之行画上句号。
回来后的两天,都在家休息。身体没有想象中的糟糕,没有太痛苦便恢复如初了。其实登山就是一个挑战自我的过程。挑战自我的体能极限和意志极限。在山路上我曾遇到一个双脚残疾,仅用两手支撑爬泰山的人,在中天门之前我见过他,后来下山没有再遇到。不知道他最终能否登顶,但他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这种精神。登山的过程是漫长的、辛苦的,但登顶之后俯仰天地,举步腾云的感觉,能让一切辛苦如云消散。“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是攀登者的最终追求。
这个原本枯燥无味即将结束的暑假因为这次行动变得意义非凡。这是一次难忘的旅程。我知道我一直在路上。我前些天去了枣庄,过些天可能要去黄山,我这几天差一点就去了乌鲁木齐——要不是有楚涵的拖累,我就毫无疑问地去了。楚涵欠我一次乌鲁木齐,长了大她要补给我。唯有在路上,才让我感到生命没有停滞,没有等待,没有窝藏,而是在一直向前。
2012年8月8日(写下这个日期才意识到这是北京奥运开幕4周年——不过显然,大家都已经忘记了。)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楚涵上学了。
楚涵爱吃方便面,早上起来我下了一包面,楚涵拿个小叉子,自己吃了半碗。她最喜欢穿白裙子,尤其是长裙。今天虽然很热,但昨天告诉她今天要带她去上学的时候,她就自己决定了要穿裙子。妻给她穿上一条白裙,扎了两个羊角辫,穿了白色的长筒袜和红色的凉鞋。她的未过门的准舅妈上周给她买了一个红色的米老鼠书包,妻昨天又给她买了一个铅笔盒,她从昨天到现在都很兴奋地摆弄着这些东西,嘴里嘟哝着:涵涵要上学了,她似乎也感到这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事件。
一切收拾停当,她背上了红色的小书包,提了一个小水瓶,满脸笑容站在门口,清晨的阳光照在她洁白的裙子上,不仅无尽可爱,甚至还有些光彩照人了。我牵着她的手走出家门。她指着停在门口的车说:爸爸咱不坐车吗?我说不远,咱走着去。她哦了一声便跟我向外走。我们走得很慢,她也很听话,没有让人抱。十分钟的路程里我们似乎说了很多话,我说到了幼儿园听老师的话,不要和小朋友吵架——如果有小朋友抢你的东西,你就告诉老师——我不担心她会抢别人的东西,因为她从小看起来像我一样是个老实且怕事的人,只会被人欺负而不会去欺负别人。她一一都答应着。她一路上也没闲着,一会说爸爸你看,那树上结着茄子,一会又说爸爸你看,那里有只猫。我最不放心的是她的挑食,不知道幼儿园的饭菜是否能吃得惯,便一再叮嘱她要好好吃饭,好好吃饭。她许是听得太多了,每当我说到“老师一说吃饭……”的时候,她就立即打断说“涵涵就使劲吃,吃青菜,长得跟爸爸一样高”。
到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已经等在门口,问了一下名字,便说“进去吧”。她说了一声爸爸再见,便转身跑进去了,这个巷子太小,她只几步便跑过去了,迅速消失在我的视线中。老师寒暄了几句便也转身走了,一扇铁门嘭地一声关上了。我没感觉自己应该离开了,我感觉我应该陪着她,或者其他远远望着她。我急切地走着,搜索每一个窗户,透过其中一扇我看见楚涵正站在那里,我叫了两声,她没有听见。我赶紧拿出手机,华为的手机真的反应很慢,在我刚刚按下录像按钮的时候,我听到老师不知道从哪里发出一声喊声“聂楚涵,这边!”,她便迅速跑开了,在我的手机屏幕上划出一条白色的影子。
往回走的路上,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像失去了什么。许是一种担心吧。她从出生到现在第一次离开家人的照顾,我不知道她会怎样,会不会哭,会不会太热,会不会被其他小孩欺负,甚至会不会被老师骂。但这一切,都是她必须要经历的,好在她对上学并不排斥,而是带着新奇和激动的。这是唯一能让我感到欣慰的地方。
突然,手机响了起来。我想,肯定是妻。打开一看,果然。她问涵涵送去了吗,我说送去了。问听话吗,我说听话。又问了一些其他的,我一一回答,不忽略每一个细节。她嘱咐中午过去看看,我说嗯。我知道,即使我把楚涵今天上学的消息告诉全世界的人,也只有妻一个人会打电话过来,这就是亲情,这就是妈妈,这个世界上最关心她的人。
在这之前,我已经托人在实验学校附属幼儿园报了名,并且已经去上了两个多月的“亲子班”。因为亲子班是有大人陪同的,所以还不算是真正的上学。本来秋天的时候就要正式上小班了,我本想让她再玩过这个暑假——孩子应该多玩一些,现在孩子们的童年已经被无限制压缩,压缩到恐怖了。我从未想过让她早早地上学,能多玩一天就多玩一天,但是一些事情使得我没法保证一个假期都能在家陪她,她不可能一个人呆在家里,所以上学成了唯一的选择,这也许是现在大多数家长共同的无奈。
我想起我第一天上学的情景。那天我被送到学校的“育红班”,被安排坐在一条凳子上。上课刚开始,我便站起来说:我要回家。于是便回家了,如此反复了许多天才终于安顿下来。楚涵现在已经去了一个多小时,老师没有打电话,她没有回来,单从这一点上看,我就要相信她是强于我的。而且她现在只有三岁,而我那时有七岁。我能侥幸记得一些那时的事,因为我已经七岁了,而楚涵在将来注定不会记得今天的事,虽然她的记性看起来非常好,她毕竟太小了。所以我帮她记下这些。这是她第一天上学的日记。第三人称的日记。她将来会看到这些。她会感兴趣的。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2012年7月25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从这天开始,家里的玩具开始安静下来,电视开始离开少儿频道,沙发不再那么乱——就在我敲这些文字的时候,父亲坐在那里,边看电视便念叨:涵涵上学去了。我是听到了的。其实我也在念叨。否则就不会有这篇文章。家里缺少了她,似乎空了下来,虽然她此时就在距离我一公里外的地方。但只要她不在我身边,这种空荡荡的失落就会蔓延。我想象她现在正在和小朋友们快乐地玩耍,或者在瞪大眼睛认真地听老师讲课,这种想象逐渐变成一张清晰的画面,我几乎能够看到了,她就在那里。
2012年7月25日中午
黄员外病了。
人老了总会病。黄员外才六十三岁,按说还不算老,但不知怎么的,就病得不轻了。而且比较奇怪的是,村子里的所有人都知道老黄病了,而且病不少,而且不轻,也许黄员外自己也知道自己病了,但他一直不承认。许是要面子,或者是传说中的“讳疾忌医”,总之是不敢承认的。偶尔他也自己说,我不太舒服。但别人问他什么病的时候,他总是说,问题不大。
黄员外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你就看这个姓,和皇谐音,也算半个皇族的,他也争气,对得起这个姓,在村子里富甲一方,甚至还有些霸道。他的发迹很简单,村里原来有个地主老姜,本是财大气粗的,后来子孙不肖,欺男霸女,村民群起攻之,灭了姜家,老黄当时提着斧子跑在最前面,而且侥幸没有被姜家的狗咬死,于是便成了英雄。之后他继续提着斧子到处转悠,便收了姜家大部分田地,收起了租子,便俨然也是个大家族了。
有钱的人最怕死。有病了,虽然不敢对外承认,但自己心里是清楚的,不仅清楚,而其是害怕极了的。虽然坐拥万贯家财,虽然子孙枝繁叶茂,但这些都换不来命。黄员外有些怕了,便真想治病了。
先是找了村里的一些大夫。大夫们看了,有的说肉吃得太多营养过剩了,有的说大烟抽多了身子要烂了,还有的说房事过度身子虚了。也有一两个说是为村子操心太多劳累过度了,不过都被黄员外乱棍赶出去了。黄员外知道这些大夫很多都没有胡说,上面说的所有病,许是他身上都有。但他却不相信大夫们的方子,具体说他们不相信那些大夫,那些大夫们个个心怀鬼胎,有的瞅上他家的地,有的瞅上他家的房,有的惦记他家的粮食,有的看上了他的姨太太——不管大夫们有没有这么想,起码黄员外是这么认为的。
黄员外打听了一个偏方。
这个偏方他是笃信的——不由得他不信,病日复一日地重,哪怕乱投医,也要试一试的。他决定召开一个家族大会,宣布治病。
黄家上上下下百十口子人聚到了一起。上到老太君大太太子子孙孙,下到门子厨师保安队员。老头子咳了一声,说:我病了,要不要治。
要治!百十口子人异口同声,声音异常洪亮干脆。
我打听了一个偏方,打算试一试,你们说行不。
行!百十口子人异口同声,声音异常洪亮干脆。
这个药有点难,怕不好弄。
咱有的是钱!百十口子人异口同声,声音异常洪亮干脆。
是这样,要用老太君一碗血,就着老大一块肉来吃。你们说行不。
百十口子人鸦雀无声。
老太君年纪大了,一碗血不要了命么。有人这么说。老太君正襟危坐,闭目养神,俨然神圣不可侵犯。
这样的话,大夫说了,用老大一碗血,老二一块肉,也行。
老大嘴撇了一下,没有说话。老二急了:爹,你的命是命我们的命不是命吗!
黄员外有点急了:用儿子一碗血,用孙子一块肉,也行!
大家忽然叽叽喳喳嚷开了,儿子们个个义愤填膺,孙子们各个咬牙切齿。看那架势恨不能吃老头子的肉,喝老头的血。
黄员外长叹一声:实在不行,是人血就好,是人肉就行。你们说,用谁的。
稍微的停顿之后:老白!除了老白以外的百十口子人异口同声,声音异常洪亮干脆。
老白哆嗦了一下,还没等说什么,一帮门子冲上来,按住老白,有的放血,有的切肉,不一会功夫,齐了。
老白是黄家的佃农加长工,从出生那天就欠了黄家一屁股债。此刻他正躺在地上抽泣。好在只放了一碗血,切了半斤多一块肉,命还在。
老爷子,您请服药!百十口子人异口同声,声音异常洪亮干脆——就连躺在地上的老白,都觉得自己干了一件救死扶伤的好事,竟也附和着说了一句:请您服药。
也许是习惯了,黄员外在服药的时候很自然,一点也没恶心呕吐或者反应过敏。血不需要炖,肉也不需要煮,就这么趁着新鲜活生生吞下去,口感和疗效都不错。
黄员外吃了药病情还真减轻了。
于是每隔半年,黄员外就服一次药。
但终究是佃农的肉,比老太君和儿子们的肉比起来,药效相差甚远,虽然每次都能暂时缓解病情,但终究不能根治。就这么维持了大概十来年,或者二十来年,或者更多年,总之之后老白死了,黄员外,也死了。老黄家总之渐渐的完了,村子没有了提着斧子到处转悠的人,竟也渐渐的清明起来了……
2012年7月5日夜
我二十九岁那年
第一次玩万花筒
它让我明白了一个可怕的道理
眼见不一定为实
2012.6.27
我最近忽然无梦
困扰数年的失眠
不治而愈
本该值得高兴吧
我却害怕了
不做梦
比失眠更可怕
梦想带来抗争
抗争带来失败
失败带来绝望
我竟然发现
梦想破灭
比没有梦想更可怕
求求撒旦 耶稣 佛祖 玉皇大帝
让我再梦到你吧
就把这当成我的
最后且唯一的请求
2012.6.18 夜
我不见她
已是三百多天
今天见了
精神分外清爽
仿佛过去的三百多天
全是白活
2012.6.8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沉重的原因,不是怕死。而是不堪承受之重。
曾经,年轻的我,狂妄地说,老了怕什么,该死就死,老而不死是为贼。人寿有限,将死则死,何必强求。人生不在乎长度,而在乎质量。
然而,慢慢地,我发现,没这么简单。
人可以老,也可以死,但关键是,老而不死。
不是想死就能死。之前,我曾对很多人说,如果老了,身体的零件不行了,死就痛快地死,别给后代添麻烦,别浪费社会资源。人寿天定,怕啥。然而,最近我看了电影《桃姐》。我恐惧了。人,不是想死就能死。死需要理由。感冒不能死,发炎不能死,瘫痪不能死,帕金森——痴傻,也不能死。人可以不怕死,但不能求死。于是我知道,有介于健康和死的中间状态。这个中间状态,最可怕。
在农村,我见过一些老人,他们不怕死,他们在60岁之后就开始建造墓地,打造棺材。我的亲奶奶,在死之前将近10年就将棺材做好了,并且放在自己的屋子里。他们不感到碜得慌,他们坦然面对死亡,他们把死亡放在嘴上。然而,当他们生病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延续生命,而不惜忍受病痛和医治之痛。他们不是怕死,而是不能轻易死。
既然如此,就有一个生命的存在已然基本没有意义但还必须存在的过程。
人人都会老去。
能蹦能跳的时候,耻于被人照顾。然而年轻不是永久,总有行动不便的时候,行动不便并不代表死亡,所以需要延续。总有脑子糊涂的时候,脑子糊涂不等于死亡,因此需要延续。总有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生活不能自理不等于死亡,因此还需要延续。甚至,当糊涂、当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想死,都死不了。喝药,上吊,割腕,跳楼,都需要基本能力。当基本能力都丧失的时候,死,就很困难。既然生不如死但死不了,就需要依赖别人的照顾。因此,任何人都不能狂妄地认为我不会为别人和社会增加负担。一定会增加,必然会增加。因此,有后代,就显得有意义。
《桃姐》中,桃姐没有后代,但有一个好的雇主。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于是就有了养儿防老。看来,孩子的意义就在于自己老去的时候。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因为生命有限而血脉无限。
每个人都会老去。我很感慨。
2012年5月19日深夜
在广阔世界中的渺小
我见证着你的卑微
像草一样
在喧嚣世界中的安静
我聆听着你的沉默
像草一样
在脆弱世界中的坚强
我压抑着你的生命
像草一样
在聚散离合的流光里
我热爱着你的朴素
像草一样
你是我的父亲
我的奶娘
我的大地
我的天空
我的宇宙
我的根
我一向不习惯赞美
但对你
我五体投地
2012年4月23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