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喜欢躺在被窝里听大人讲故事,土话叫“拉呱”。除了故事,也会跟着学一些童谣,有的大概都称不上“谣”,因为“谣”怎么也得有点曲调,有些童谣其实就是些顺口溜。农村很多妇女,没上过学,大字不识,却祖辈相传,学来很多这种“童谣”。上一代讲给下一代听,一代代这么传下去,也不知道最初的作者是谁,也不知道中间又经过了多少演绎。大多数的童谣,长大了之后都会慢慢忘掉,或者只记得只言片语。但我想,虽然忘记了,但它们肯定曾发挥过作用。就像饭吃进肚子里,有营养的部分消化掉了,没营养的排泄掉了,饭是找不到了,但不能说饭没有起作用。童谣在潜移默化中发挥着一种十分原始的教育的功用。
楚涵从很早就开始学话了,现在俨然已经基本可以与大人交流。她可以记得昨天甚至前天的事,可以准确喊出数十种动物的名字,也可以一字不差地唱完好几首儿歌。也许这么大的孩子,记忆力的发育应该达到这个程度了。但我却总感到一些惊异,进而以为她有学习上的天赋。按理说,是时候教她一点唐诗宋词什么的了。我记得T君的孩子像她这么大的时候似乎已经咿呀地背诵一些《春江花月夜》了。但每当我要教她,看着她瞪着大眼睛,听到我朗诵“春江潮水连海平”时的满脸疑惑的表情,我就不忍心了。她知道什么是春,什么是江,什么是潮呢?她哪知道为什么“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呢?所以每到这时,我又不忍心了。纵然她在我反复地训练或在糖果的诱导下勉强可以记下了,但记下的也不过是“CHUN JIANG CHAO SHUI LIAN HAI PING”这么一串发音而已。这种纯粹机械的记忆,除了勉强锻炼一点大脑,和记忆一个简单的狗狗猫猫没什么区 别。所以,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又不勉强她去学些什么东西。
其实完全不用担心缺少科学的计划会使孩子的学习出现真空,孩子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相反是在一个极为复杂的世界里。他们自己会懂得去伪存真,去学他们想学的东西。他们只要在成长,就在不断学到东西,比如,我意外地发现,她学会了好几首童谣,这可不是简单的童谣,已经有一定的篇幅了。这完全归功于她的奶奶,一个基本只会写自己名字的农村妇女。这些童谣我小时候都听过,有的至今还颇有印象。以前只是当作顺口溜来念,现在仔细琢磨琢磨,这些看似肤浅的东西,未尝不是蕴含了一些教育的元素在里面。且看两篇。
未命名童谣一·月亮圆圆
无名氏
月亮圆圆,出来神仙
神仙卖菜,出来奶奶
奶奶烧香,出来姑娘
姑娘磕头,出来小猴
小猴作揖,出来小鸡
小鸡嘎嘎,要吃黄瓜
黄瓜有种,要吃油饼
油饼喷香,要喝面汤
面汤希面,要吃鸡蛋
鸡蛋噎人,要吃牛皮
牛皮一包毛,要吃樱桃
樱桃有尖儿,要吃县官儿
县官儿太大,不吃罢了
未命名童谣二·喜鹊叫喳喳
无名氏
喜鹊叫喳喳,捎信儿把鸡杀
鸡就说,又下蛋来又抱窝,杀我不如杀个鹅
鹅就说,下蛋累得脖子长,杀我不如杀个羊
羊就说,四条白腿往前走,杀我不如杀个狗
狗就说,看门累的喉咙哑,杀我不如杀个马
马就说,驼着鞍子下九州,杀我不如杀个牛
牛就说,耕地累得一腿泥,杀我不如杀个驴
驴就说,————,杀我不如杀个猪
猪就说,一瓢水来一瓢糠,哼唧哼唧见阎王
未命名童谣三·小蚂蚱土里生
无名氏
小蚂蚱,土里生
前腿刨,后腿蹬
一蹬蹬到北京城
北京城里好年景
碰上姥姥烙油饼
给舅舅,一大半
给外甥,一丁丁
不怪姥姥舅舅事
单打妗子小妖精
第一首,看似十分滑稽,但这正是适合小孩子的口味。我没研究过这方面的理论,但是深深地知道孩子对世界的认识很多时候是从动物开始的,而且孩子们眼里的动物和人一样甚至比人还要可爱。孩子天生就会过家家,喜欢看卡通片,这应该反映一种科学的认知规律。这首童谣将身边的一些事物串联起来,有月亮、奶奶、姑娘和各种事物,有磕头、卖菜、作揖各种动作,貌似呈现出一片奇异的童话世界,足以引起孩子们的兴趣。后半部分中,以“小鸡”的“吃”为主线,又引入了生活中的很多食品、果肴,孩子都是贪吃的,这里面的美味佳肴足以吸引孩子们。除了列举了一些吃食,相当于学习了一些“名词”之外,还体现了各种食物的特点,能够让孩子们从中了解到什么东西香、什么东西甜、什么东西噎人,这个熏陶的过程必然是十分隐蔽的。这才是真正的寓教于乐,是教育的最高境界。这里面可能有个词要解释一下:希面。老家方言中表示很甜叫“XI甜”,表示很“面”叫“XI面”,这个XI字不知道是哪个字,就用了这个代之。
第二首,更加妙趣横生。不仅如此,还十分具有文采。以一个“喜鹊叫喳喳”引出后面的一系列对话,用一种工整的句法巧妙地串联起了常见的家禽和家畜,这些动物在农村在古代应该都是很容易见到的。这首童谣将各种动物的特点和对人类的贡献形象生动而且精炼地概括出来,以如此朴素的形式表现出来,不能不说非高手不能为之。孩子们听得久了,记住了,对于他们认识世界必然是大有帮助的。遗憾地是我现在忘记了“驴”的话,只好用几个省略号代替,回头问问楚涵。还有一点是,最后猪的话中,原话不是“哼唧哼唧”,而是“zhui er zhui er”,这无疑是一个拟声词,但我没有知道合适的汉字。这个词形容的是猪被屠宰时发出的叫声。“哼唧”显然不太合适,但暂且表示个意思吧。
第三首则复杂一些了,以小蚂蚱开头,采用拟人的手法,跳跃性地完成了一个简单的故事,除了体现了一些亲戚称谓之外,还加入了一些人情事故。小孩子念起来,大概也能粗懂一点亲情厚薄,人情冷暖?
我还记得很多童谣,但只是一些残片,实在无法整理出来。虽然这些童谣的内容大都略显陈旧,但也不失传统和朴素。今天给孩子们念起来,也还很有一些味道。我想这大概不能算是封建糟粕,还是有必要整理一下的。倘若有暇,能够踏遍神州,遍访民谣,整理成册,未尝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文化活动——不过,这大概基本上不可能做到啦。
2011.8.1日至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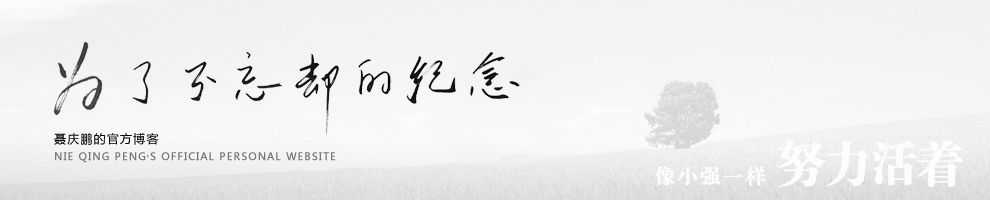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