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十一假期比较疯狂,完成了一次期待已久的,同时又十分难忘的西行壮举。与一群朋友搭伴,十四人开三辆车,七天里穿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四个省,往返4500多公里,在洛阳、西安、汉中、成都均有小驻。时间所限,马不停蹄,一路下来,虽有旅途奔波之苦,但所见所闻,所经所历,又不断戳动原本日渐麻木的神经,让心朝着年轻生长。况且不光有高朋同行,还有妻女陪伴,其乐融融,这是一段不折不扣的寻梦之旅。每当远行,都能倍感中国大地之广袤,日照一地之局促。倍感世界变化之万千,自己井底之蛙之有限。倍感历史之厚重悠远,人生之飘忽短暂。从而让自己更看清楚自己,更多的去想自己从何处而来,往何方而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旅游,相比于实实在在的风景,更多的是心灵的旅行,思想的远征。
十月一日早上出发,第一站洛阳。日照到洛阳700公里,计划10小时。高速路上没有想象中和电视上说的那么拥挤,初上日东高速还有点“节日气氛”,但过了临沂,直到过菏泽出山东,都一马平川。虽有车但不堵,虽有雨但不大,也算天公作美。早上9点从日照出发,下午5点多出山东,一路追着落日的脚步,过兰考、开封,天擦黑时到郑州。再过荥阳、巩义、偃师,晚上七点半到洛阳。吃罢晚饭时,已经晚上十点。假期的第一天,就在传说中的“高速一日游”中度过了。况且鲁豫一带,地理接壤,风情相近,除了感叹各地城市建设之大之快,一路上倒也没有太多新鲜。听说河南擅长吃面,晚饭时要了一盆,每人吃了几小碗,味道确实异于别处,获得一致称赞。至于菜肴,与鲁菜差别不大,喜大鱼大肉大油,量大实惠,只是似乎比鲁才更咸一些。在吃盐这个问题上,中原和沿海地区的差别还是十分明显的。
十月二日早起,在住处楼下早餐店里吃了早餐,一种叫做“豆腐汤”的食品。豆腐我小时候是不吃的,近几年忽然吃起来,而且颇喜欢。这种豆腐汤,倒是头一次吃,切好的豆腐条,加上忘记了牛肉汤还是羊肉汤的高汤,放上调料,再配一份手抓饼,辅以炸萝卜丸子,倒是合我这内陆长大的人的口味。我吃得很美味,妻似乎反应一般。楚涵更惨一些,长途奔波身体不适,微烧,还伴有口腔溃疡,正打蔫中。于是吃完饭又去买了点药。到了八点半,整装出发,赶往此行的第一个景点——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这个名字一定是在哪本历史课本中出现过,而且应该还在前面的彩页中有过照片,不然不会让人如此印象深刻。此行洛阳不到一天的时间,放弃了关林、白马寺等一干景点而独选此处,也是不折不扣的慕名而来了。石窟距离住处仅十几公里,但市区路况拥挤,行进缓慢,近一个小时才终于到达景区停车场。景区显然为这个黄金周做了充足的准备,人虽然极多,但秩序很好。过了一个刻有“龙门”二字的大拱门,就进入景区。石窟分东西两区,中间横亘一条伊河,水面宽数百米,绿波荡漾,有高大石桥飞架河上,车流不息,倒也是一景。
从西区起步,沿河岸往西南方向一路游来,见大小佛窟数千,造像数万不止,皆临山壁而凿,年代、大小、形制各异。佛像大的高数十米,庄严壮观,小的似手掌大小,不失精致。至于造型、流派云云,则非我这等对佛教一无所知的人所能欣赏。但一路走来,即便不信佛、不懂佛,也足以为此大观所折服。这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力量。我虽不认得形态各异的佛,但却认得字,虽然由于年代久远,整个石窟留下的刻字并不算多,但从那些被千百年岁月消磨遗留下来的斑驳文字中,仍能依稀见古人遗留的说明书。如“优填王像北龛韩曳云等共造供养”、“优填王像南龛司徒端等共造供养”,让人知道曾经有这么两个名字,联袂打造了这南北龛。还有如“宪台令史袁弘绩敬为亡父及见存母造观世音菩萨”,则见这位袁大人之一片孝心。还有一尊简陋破败的小佛像,旁边几个歪歪扭扭的小字“僧惠贤敬造”,让人仿佛看到一位虔诚的佛门弟子在此忙碌的身影,我甚至都猜测这尊看起来不太专业的佛像和字迹是这位惠贤和尚自己刻出来的。虽然比之于整个石窟中最大的、由大唐女皇武曌捐脂粉钱所造大佛,这些小佛像只是高山一草,但不论他们是官是民,是僧是俗,但都在这里寄托了某种美好的愿望和信仰。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名字都已湮没无闻,即便是旷古一人的女皇帝也已零落成泥,但留下的石头却传承千年,成为全人类的文化财富,他们竟也随着这石头而暂时不朽了。实施这样的工程,在当时大概是成本很高的,但时至今日仍能为当地人创造巨大的财富。这世上大概只有信仰,才能创造出这种旷世大观了。
文字除了能传递出遥远年代的信息,有的甚至记载了不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但更多的是传递着汉字文化和艺术的美感。南门出来,一侧的墙壁上展示了大量石窟刻字的拓片,曰“龙门二十品”。龙门石刻书法精品,以魏碑为最,我虽是书盲,但见这些来自一千五百多年前的瑰丽文字,古朴端庄,神韵四射,仍深感震撼。细读一旁的说明,方知此处的魏碑一直被视为魏碑书体的法帖范本,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地位崇高。如此说来,能亲临一睹,倒是十分荣幸的了。
西区出来,往东过一大桥,便是东区。因时间所限,加之人疲脚乏,所以放弃了东区,径直向北,过了香山寺,便来到白园。这是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地,无论如何要进去瞻仰一下的。曲径攀岩,越过一片清幽之地,遥见一片苍翠之中,一座不高的小山,名曰琵琶峰,峰顶便是白居易的墓了。巨大的坟茔规矩整齐,下有矮墙,上面野草茂密,杂木数株。绕到墓前,一通石碑,高约四五米,上书六个楷书大字“唐少傅白公墓”,遒劲有力,落款为康熙四十八年汪士鋐题。右侧还有石碑数通,都是前朝名人故吏所题,记述时事,无暇细察了。伫立墓前,心潮澎湃。这位从小就在课本上、唐诗中无数次看到名字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就长眠于此,就在我眼前几米远的地方。一种强烈的感觉压迫着我,让我有俯身下拜的冲动。但往来不绝的人群使我压制住了这样的想法,心中却不禁默念起白公的名篇,《琵琶行》《长恨歌》《卖炭翁》……这位将近一千两百年前的巨匠所遗留的文化经典,远远比这墓碑和坟茔高大壮丽的多,让我这样的后世学生,只能顶礼膜拜和无限仰望。他们曾是那么空前绝后,那么璀璨的存在着。
洛阳的行程,仅有一天。白园归来,便直接启程,赶赴西安。虽囿于时间,许多地方不能前往,颇多遗憾,但这一次之所见所闻所获,已足以为多年之慰藉。洛阳,我还会来的。
2014年11月13日至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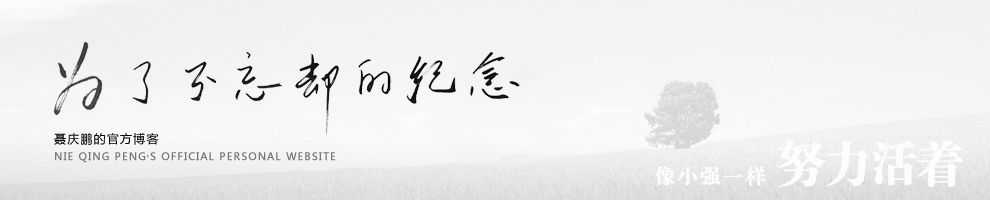

好文章,内容义正词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