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常人的世界里,出现一个疯子,是很悲哀的事——无论对疯子还是正常人而言。
——题记
车颠簸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每到一个岔路口,我就不得不减速或者停车,仔细辨认方向。不仅我已经数年没有来过,就连母亲都已不记得路,她一共下车问了三次路,才终于找到那个叫做西王沟的村子,在村子里又问了两次路,才终于打听到小姑的家的确切位置。狭窄的胡同,车已不能通行,母亲步行去找,我提着一兜苹果跟在后面,周围则是村人们好奇且诡异的目光,大概她家,已经很久没有亲戚登门了。
我们的努力最终还是白费了,大门紧锁,她没有在家。一位邻居说,可能去田里收玉米了。我说还等等吗,母亲想了想,说,不等了,走吧。
于是,我又没能见到她。虽然我似乎没有太多想见她的理由,但隐隐有种感觉,想知道她的近况。这次的不遇,只能让我对她的印象,继续停留在上次见面时的,那半头白发、略带微笑和木然的神情。
一 缘起
如果时光倒流到三十二年前,她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那一年,母亲从四十里地之外的冯家村嫁到这个家里来。十六岁的小姑倚在东屋的门框上,看见母亲进了门,朝着母亲羞涩地一笑。母亲常说,小姑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话不多,对谁都是笑呵呵地,善良而文静。
如果没有那一天,我想一切是应该另一幅样子。但命运就偏偏以一种匪夷所思的形式转了个弯。那是村里一个远房三叔家小名叫“幸福”的大儿子喝农药死掉的那天,出殡的时候,有人说,让小四也跟着来吧,幸福最喜欢这个四弟。这句话从送殡人群的前面一直往后传,传到了队伍最后面的小姑那里。这似乎是一个巨大而且无法继续推脱的使命,小姑跑回村里,背起只有三岁的小四,去赶送殡的队伍。也许是过于着急,或者是后来村人所传说的沾上了邪气,小姑跑到村西头她平时最熟悉的那个岔路口时,竟忽然迷了路。村里有人见他背着四弟朝东走,走了二三里地后在一个地头上呆坐下来,后来竟呜呜地哭了。
这天之后,小姑说话更少了,而且经常会说害怕。有时候到了晚上,便钻进奶奶的被窝,让奶奶搂着。奶奶不信邪,说她装病,便呵斥她,她便更害怕了。如此大概过了两三年,她竟开始说一些胡话了。也许因为大部分时间里她仍是正常的,所以虽然也时常给她买些药吃,但没人把她当病人。她的病就这样不好不坏。直到有一天,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小姑躺在里屋的床上睡觉。忽然,她从床上坐起来,伸了一个怪异的懒腰,然后“嘿嘿”地笑了几声,以一种怪异的声调说“我在深山老林里修炼,可热死我了”。然后当着全家人的面撩起上衣呼呼地扇风。
全家人都呆住了,母亲说,她感到头皮一阵发麻。
小姑真的病了。
二 求医
病了就得治。从村里到乡里,从乡里到县里,从本县到邻县,奶奶带着小姑四处求医问药,去了无数地方打了无数次针吃了无数种药,偶尔也有好转一些日子的时候,但终又会复发。精神病和其他病不同,一旦得了这种病,便仿佛得了瘟疫,人人都争相躲之不及,虽然她只是说一些胡话,做事乱了条理,但并不会打人毁物。起初兄弟姐妹们还有些可怜她,给予一些帮衬,日子久了,便渐渐麻木起来。大家都说,治不好了,就这样了罢。
爷爷只是喝闷酒,奶奶抚着小姑的头说,不行,得治,小爱还没结婚呢。确实,村里和她同龄的女孩,大都已经有孩子了。
于是努力仍在继续,只是困难更甚。奶奶又带着小姑去了八十里地之外一个镇子,那里有所有名的精神病院。起初家里几个大哥轮流骑自行车去送饭,每隔十天半月送些干粮去,后来各家农忙,送饭的频率越来越低,到最后几乎要断粮了。那年的秋天,几天没有吃饭的奶奶带着小姑去医院外面的田地里拦地瓜。秋收结束的田野里,六十岁的奶奶用一个废弃的搪瓷茶缸做工具,四处挖掘,寻找遗落在地里的地瓜。这场景我没见过,家人也没见过,奶奶也没有说过,医院的人把这情景说给后来终于去送饭的人。大家知道了,都有些沉默。
三 初恋
小姑失踪了。
虽然治疗从未放弃,但效果始终难以如意。好的时候,便在家里,有说有笑。犯病的时候,便送到医院,打针吃药。按说当打针成为一种习惯,就应该不再害怕。但她还是害怕,经常在打针后用双手抱着头,这竟也渐渐成了一种习惯姿势。有一次,小姑在县里住院。旁边病床上有个老头子得了癌症,有个二十多岁的同样有些腼腆的小伙子天天伺候着。日子久了,小姑和那青年便有些交谈,似乎还很有默契,似乎,小姑慢慢又高兴起来,她的病,竟似乎好得快起来了。以至于不久,在那老头子还没死的时候,小姑就要出院了。
但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小姑就失踪了。
一连几天,没人知道该去哪里找她。奶奶急哭了,其他人只是叹息。母亲说,我去找找吧。母亲去了医院,围着医院转了几圈,最后在旁边一个林子里找到了她。她和那个青年坐在一块石头上,还是那样习惯性地抱着头。母亲叫了一声:小爱!她抬头看了看,叫了一声:三嫂。便跟着母亲回家了。
我曾问母亲,如果你不去找她,她的病会好吗?会跟那个人私奔吗?母亲不说话。是的,如果是我,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四 捉鬼
年龄越来越大,病却这么不好不坏。每个人的耐心都在销蚀。奶奶终于动摇了,说,去请小璐吧。
小璐是村里的大夫。他是西医,却也卖中药,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从老爹那里学来一套驱邪避鬼的本领,擅长捉妖斩怪。村里早就传说,小姑的病是“虚病”,邪气附体。但奶奶不信,她一生不信邪,所以一直相信医院。但到了这个份上,再固执的人,也足以折磨到崩溃,她妥协了。
小璐来了。
他几乎没有太费劲就确诊了,很坚定地说,有东西。然后说,下次,她再犯病,说胡话的时候,快去叫我——要偷偷的,别让那东西知道——我拿住它。
果然有了下次。
那天,一家人在堂屋吃饭,母亲在灶房烧火。奶奶忽然神色紧张地从屋里出来,对母亲说,快去请小璐,犯了!
小璐让母亲走在前面,他猫在后面,怕让那东西看见。进了屋,小姑正背对着门口吃饭,小璐一把推开母亲,冲上去用胳膊卡住小姑的脖子,在她后颈、前胸和右手腕子上各扎了一针。母亲说,不愧是大师,扎针的速度很快,以至于一屋人都没有看清。小姑拼命挣扎,两手乱摆,以至于手腕子上的钢针都弯了。小璐高呼,快按住这东西!一屋人一拥而上,把小姑死死按住。
小璐怒声呵斥:你是什么东西,来这里害人!
小姑不说话,只是用尽浑身的力气挣扎,虽然无法移动半点。
小姑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抖动,三根针竟渐渐要掉落下来,小璐赶紧又重新按住,大声说,好个东西,敢拔我的针!小姑也恶狠狠地说:你捉不住我!小璐说,我非要捉住你!
如此的角力持续了大概一袋烟的功夫。不知道是小姑没力气了,还是那东西屈服了,小姑渐渐平静了下来,躺在地上不动,只是喘气。小璐让大家出去,他和那东西进行了会谈。当时在场的人不多,不太清楚会谈的具体内容,总之到了最后,小璐神情轻松地走出堂屋,对大家说,问清楚了,是个夜猫子精,以前在山里修炼,现在在村大队院子里的那棵电线杆上住,已经祸害了好几个人。大家忙问那该怎么办呢。小璐说没事了,我跟它说好了,它不敢来了。
捉鬼圆满成功,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而小姑的病,竟然真的渐渐好起来了。有相当长的一些日子,除了说话很少,已经和正常人几乎一样了。持续数年的疯癫生涯,似乎真的要和小姑告别了。这个大家庭,似乎真的要重归正常了。
五 抗婚
病好了,人也已经二十八岁。这几乎已经捅破正常人家女儿出嫁的底线。一家人都着急起来,好心的村人也来帮忙,大家纷纷出谋划策,介绍了一个又一个。不知道是精神还有没完全恢复,还是没有忘掉医院认识的那个青年,小姑竟一个也不同意。在第N次相亲又无果而返后,爷爷怒了,扯起一根棍子,怒骂一声:你以为你自己多好吗,这个看不中那个看不中!然后一棍子打过去,棍子断成两节。小姑没有躲,也没有哭,也没有说话。
不久之后,她就嫁到那个十五里地之外叫西王沟的村子去了。
小姑夫是村里一个远房亲戚的远房亲戚,姓刘,是个木匠,个头不太高,长相还不赖。九十年代初的青年,刚开始学习时尚,留着洋头,穿的也光鲜。这样一个条件,按说不会找一个有病史的人,但据说他的家庭成分不太好,祖辈是地主,老爹早死了,留下四个儿子,三条是光棍,其中一个上吊死掉了。虽然知道小姑的病史,但还是看在病已经基本痊愈而且虽然有点傻但总比没有强的份上,还是接受了。
出嫁的那天,一家人都有些紧张,希望她的病是真的好了。一切进行的还算顺利,只是到了刘家,进了洞房,在床上坐了半晌之后,她对围在边上看热闹的姑父的一个徒弟说,她饿了。这徒弟便去给她找了一些吃的。她吃完之后说,还饿。于是这徒弟便有些疑惑,于是便慢慢传开来:她的病还没有彻底好。按那时候的婚俗,新娘子结婚当天进了洞房就不能出来,也不能进食,过了洞房花烛夜,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出来。于是为了避免去茅房,提前一两天就需要开始绝食绝水。到了结婚这天,饿是肯定的,但小姑说出来了,而且还吃了,不光吃了,还吃了两次,她便暴露了。
也许从这时起,这个并不容易组建起来的家庭,就已埋下了注定风雨飘摇的祸根。
六 日子
我印象中的小姑夫,不是恶人,甚至还带点文雅。但他对小姑并不好。婚后的一段日子,也许也曾有过甜蜜,只是不知道持续了多长时间。小姑的病终究被证明还没有全好,能干一些家务,但很邋遢,经常失误或出错。姑夫起初也许有过耐心,但慢慢便暴躁起来了,后来据说经常打她——一个病人,打她有什么用呢,只能让她更害怕,进而更加不正常。
纵然如此,他们还是有了孩子,三年里生了两个,一儿一女。所有人都曾担心的孩子,不仅被证明很正常,而且都很懂事,大家都松一口气。但小姑照顾孩子,却没人能放心。事实也证明,她无法胜任。母子的境况很辛酸,生活艰难而惨淡。亲戚们经常去看看,回来之后大都叹息不已。母亲曾在冬天去给小姑的孩子做过一条棉裤,换下了那条已经不知穿了多久,尿透多少次,结着冰凌,还爬满了虱子的旧裤子。母亲从不愿多提那时她所见的情况,也许是不忍。
那时候的小姑夫,还经常到村里来。他曾在十五年前用我家那棵梧桐树为我们做了一组大衣橱,并用他不知道买的还是借的照相机给我们家人以及家里那只青山羊照了相,我推着他那辆崭新的变速自行车,站在家里的那棵月季花前留下了一张照片。那些照片现在都还沉睡在老家相框里。那时候的他似乎还比较有喜气,家里人见了面,大都问他小姑怎样,孩子怎样。他大都不太说话,只是说,还那样。每个人都在说,疯也罢,癫也罢,总算是两口子,总算是养活了儿女,将就着吧,好好过。他大都不太回答,只是抿着嘴,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很轻的“嗯”。我因此感觉他是一个老实人,虽然许多年后,他的一些作为,已不值得让我继续尊重。
日子就这么过着,不温不火。虽然不算美满,至少看起来,还都比较稳定地活着。
七 人祸
如果没有这次人祸,也许一切还会向好。但这只是如果。
搞计划生育的人来了。这是很正常的。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也许貌似可能已经可以算超生了,倘若不是看在傻子的份上,大概早已经按照他们一贯的方法拆房子搬家具抓人株连九族了。他们表现出罕有的人道主义,没有拆房子,只是要求立即结扎。“结扎”这个词我是后来上了很多年学才知道的,之前村里人不论从发音还是从含义上,都一直误用“截闸”这个词。是啊。在人体小腹部里面那个叫什么管的位置扎上个绳,截住罪恶的生殖物,可不就像大坝的闸门截流那样吗?
小姑被他们拉去了。当时具体用的什么动作我不知道,所以只用了拉这个字。但我想强迫一个不愿意结扎的人去结扎,采用的手段一定不会太温和,就像我见过的其他村里很多人被都是像牲口一样拖走的一样。那个时候,倘若小姑父能站出来接受结扎,可能小姑能免此一劫,但根据常理推断,他怎么可能站出来。小姑在惊恐和哀嚎中接受了手术。手术完了,她的精神,也几乎完了。在手术后不知道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晚上,她跑了,光着身子,赤着脚。刀口挣开了,血顺着腿流到脚上,然后沾到路上。家人不知道是循着血迹还是按照路人的指引,第二天在十里地之外的镇上找到了她。她当时蜷缩在一个墙角里,正在啃一个好心的路人给的馒头,双手都沾满了血。
从这之后,我想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都应该明白,她真的没有希望再好起来了。
八 缘尽
当原本虽然微弱但毕竟还存在的希望之火被彻底浇灭,我的小姑夫,大概也到了作出大家意料之中的选择的时候。他来了,找奶奶,说,离婚吧。奶奶说你的孩子你还管不?他说管。你的家你还要不,他说要。奶奶说那好,你还要孩子,要家,就得要我这闺女,婚不能离。小姑夫沉默半天,走了。
从这之后的若干年,不论是我们,还是他的老婆孩子,没人再见过他。据说他去过大连,青岛,以及南方一些城市,还似乎出国劳务了几年。听他村里人说,他每到一个地方,似乎都能找一个老婆,当然是没结婚但在一起过日子的那种。他打工赚的钱,似乎大都也就这么消耗掉了,也许也曾往家里寄过一些,只是没有听说。六年前奶奶死了,他出现了一次,但很匆匆,家里人对他也没有什么好言语,白眼和挤兑是少不了的,于是很快,他又消失了。直到现在,再也没有踏入这个家。
小姑自己,是万万无法撑起这个三口之家的。家里的家务,脏一点,乱一点,姑且可以凑合着过,可田里的农活,孩子的学费,都是无法将就的。好在刘家还有个老三,光棍一条,住得又不远,于是便能经常照顾一下。不论他是出于对孤儿寡母的怜悯,还是出于兄弟之间的扶助之责,还是其他什么目的,总之,一个男人的帮助可以让这个家继续维持下去,总算是好事。小姑和两个孩子受他的照料,总算都活着,虽然干瘦纤弱一点。两个孩子总算上了几年学,虽然初中就被迫辍学了。孩子们总算基本长大成人了,虽然一切都还没有着落,只是流落在各个城市的角落里做一名低龄农民工。
这样的日子,一年一年。伤痛在慢慢抚平,孩子在渐渐长大,故事在悄悄遗忘。
九 流光
上次见小姑,是去年春节。当时大伯家一个堂弟结婚,她去了,而且去得挺早,也随了礼,而且据说随得不少。她头发已经白了一多半,脸上胖乎乎的,好像胖了点,从说话来看好像精神状态还不错,基本交流没有问题,只是还是略略有些迟钝。也许这么多年虽然辛苦但还算平静的生活,让她的病也慢慢减轻了。总之她给人的感觉已经不是疯的,只是略微带点傻气。
岁月总是不可抗拒地改变着每个人。她带走或者掠去的,从来不曾再归还。她带来的,有些会很快失去,有些则永远相随。有些人永远不值得再期待。有些人,则是未来。
2011年10月2日至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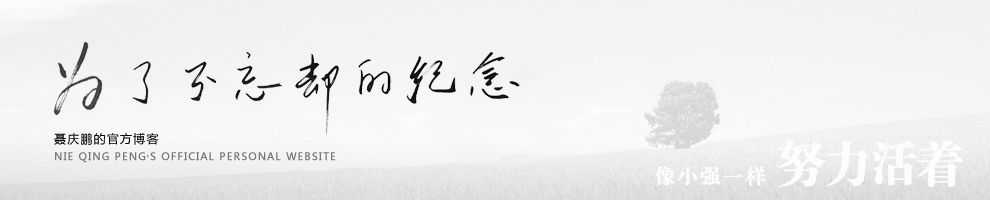

看完这篇日志,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心底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也许在被强制结扎时患难夫妻的相互扶持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也许我们的多一点的关心能让小姑变得更美好一些。大概家庭的变故,最受影响的就是孩子,在自己做了母亲之后,更是深有感触。看到写孩子那一段,几乎都要哭了。。。
不过大概是安定的生活,让小姑也安稳起来。也希望她以后的生活也能够安稳、美好。
TO:crystalapple
感谢关注及真诚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