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生命化作那朵莲花,功名利禄全抛下,让后世传颂神的逍遥,我辈只须独占世间潇洒……"这是电视剧《封神榜》片尾曲中的歌词。《封神榜》不是表现佛家思想的作品,但此一插曲的歌词却深得佛家精神的意趣。佛家看穿世间一切,绝少流连,但佛家对世间之物亦有所挚爱,而最爱莫过于莲花。佛祖坐的是莲花,手持的是莲花,口头常讲的是莲花,佛经中更有以莲花命名者,如《妙法莲花经》。佛门中有人道破了佛家对莲花情有独钟的天机,此妙真知性,本然清净,岂容外物之所污染?故佛以莲花为喻。莲花生于淤泥中,而不被淤泥之所污染;此真如妙性,在众生烦恼心中,而不被烦恼之所浊乱。(道衍《道余录》)
佛家之所以独钟莲花,是因为视莲花为真如的象征。真如亦称如来,指佛性。莲花生于污泥之中,但光艳灿烂,亭亭玉立,出污泥而不染。真如在人心中,却不被人心的烦恼所浊乱。这里面所包含的佛门意旨,是佛教大乘派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
"小乘佛教以无余涅磐召唤众生,竭力宣扬永绝生死轮回之乐,但迷恋生命毕竟是人之常情,因此要人相信灰身灭迹,生命永绝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死后境界有无上妙乐,实在是戛戛乎难哉。任何一种人生的觉悟,任何一种生命的超越,都不能背离人性倾向和现实要求太远,否则境界再高也难免被世人遗弃而成为绝响。追求生命的超越,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安身立命,并从中获得心灵的抚慰,感受到人生的幸福。因此,当佛家意识到了小乘佛教的生命超越取向太过出世离俗,难以唤醒广大众生的觉悟和追随热情之后,便有了大乘佛教将涅磐境界从死后世界向现实世界的转移。大乘佛教认为,涅磐的种子或基因佛性就存在于世人的心性中:"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如来即在众生县内";"泥洹不火,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的佛性被无明所遮蔽,只要能在认识上法除无明,排除各种驳杂污染的思虑和烦恼,就能使真如显现,成就涅磐。这里,大乘佛教肯定了涅磐的此岸性,并且把涅磐基因种植在大众心性中,从而使佛家的超越取向更具群众基础。
那么,现实地成就涅磐有何妙处呢?这就是拥有常、乐、我、净四种胜境。如《大方等无想经》所说:"–切众生皆有佛性,其性无尽。……今诸众生明见佛性,得见如来常乐我净。"大乘佛教反对小乘佛教否定常乐我净为人生基本要求的看法,强调涅磐境界具有常乐我净四种美好属性,主张追求和找到人生真正的常乐我净。获得了常乐我净,就是获得了涅磐:而获得了涅磐,就能在任何一种人生环境中,在任何形式变化内,始终保持常乐我净。佛家在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大千世界,苦海无边,经尘滚滚等基本社会和人生价值判断之内,转而肯定人生有常乐我净存在,肯定涅磐境界的此岸性,是在社会发展大趋势下对人心人性需要的一大顺应,是在否定中见肯定,因而蕴含着常乐我净品格的此岸涅磐对人有着现实的吸引力,对于开启人心的觉悟和帮助人安身立命有着更实际的影响与指导意义。试想,在充满逼迫性和喧嚣翻腾的现实世界和人生中,我们如果能领略常乐我净之旨趣,从痛苦烦恼中超脱出来,即使做不成阿罗汉,成不了佛,吕不也是人生一大难得的幸福?下面我们分别介绍一下常乐我净的意旨,以领略其对我们的人生意义。
(1)常:常是与无常相对立的概念。一方面,佛家以世界万物为变化不居的无常存在,劝导人们不可执著于对身外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佛家又认为作为宇宙万物本体和实相的真如是真实恒常的存在,是唯一值得人去领悟和追求的人生价值。如《唯识论》在解释莫如之意时说:"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易。谓此真实于一切法,常如其性,故曰真如。"不难理解,佛家大力贬低现实世界中所有令人意动欲躁的事物,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要人回过头来追寻佛家所开辟的涅磐境界,因而涅磐境界就必须是恒常的存在,只有常才能真,才值得人牺牲一切去追求。而从证得了涅磐境界后的实际效果看,且不说杜绝了生死轮回那种虚玄的常,就是在实际生活中,涅磐之人洗净了内心的一切杂念污染,心定神静,意念寂然,自能笃定莫如本性,不为外界变化和诱惑所动,不为思虑烦恼所扰,恒守一种生命和人生的本然常态。所以,涅磐之常、人生之常的求取关键还是在于超越生命意志,让躁动的意欲止息,达于内心的空灵澄明,消除身心对外界刺激的敏感性,虽时时刻刻有万干事件撞击于心而皆能虚怀纳之而不系于心,使佛性真心如出水莲花不为俗念和烦恼所蔽,如此则心境的恒常自能握定行为的安然。反之,如果俗念仍存,心未空灵,则绝不可能获得涅磐之常。这里讲一则苏东坡的故事。苏东坡是中国宋代著名的大文学家,他从小受的是儒家那套济世立业的教育,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由于遭受政敌排挤,官场失意,因而对佛门三宝颇感兴趣,并自我感觉在看轻俗务和政治人事的纷争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佛门境界。一天,他自以为在研读佛书上又有心得,便作了一首赞佛偈:"圣者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八风在佛家语言中是借指利衰、讥赞、毁誉、苦乐这八者,八风吹不动的意思就是说面对现实人生不为环境变迁所动心,不为种种物质和精神的刺激而改变本色。苏东坡作这首偈表面上是赞佛,但实际上是在自我表白因而偈作好后,感觉很得意,便派书僮过江送给佛印禅师欣赏。不料,禅师阅后,在其偈尾批上。狗屁!狗屁!。将原稿退还。苏东坡一见之下,怒气冲天,马上带着书僮过江,要找佛印禅师论理。当他走到禅房门前时,门早已关闭,但见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上写"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见后,啼笑皆非,深感惭愧,知道自己心态距空灵寂静、笃常难动的佛门境界还差得很远。
在变化无常的现实世界中,以涅磐之常召引芸芸众生,不能不说佛家通过自己的人生觉悟替渴望安身立命的芸芸众生找到了一处人生胜境。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人们,常常为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而不知所措",为时代价值的此兴彼衰而感到茫然,并由此而心性失常,行为失常,增添了不少烦恼和痛苦。因此,在纷乱多变的社会生活中,人们虽不一定要将生命超越的目标直指涅磐,但如果能从佛家智慧的启迪中开悟心灵,陶冶性情;以求得一份处变不惊的平常心,则也是大有裨益的。就拿当代文化人来说,许多文化人之所以在商品化大潮的轰鸣中倍觉焦虑,就是因为在社会的无常变迁过程中缺少对世界和人生真象的把握;企图驱策自己的心去追赶变动无常的现实,甚至不惜丢弃固有的志向和爱好,舍长知短地扑通下海,从而使自己滑失在起落不定的无常人生中,丢掉了文化人本来应有的价值。所以,如果文化人领悟了佛门真谛,使内心保持澹然平和,则自能做到"八风吹不动",以淡然的心性来对待社会的变化和各种诱惑,反而能够坚守文化人的人生使命,笃定自己真正的价值、人格和事业。
(2)乐:佛家的涅磐之乐是与涅磐之常紧密联系的,人生无常,故而痛苦,进入不常的境界:则定然苦去乐至。但涅磐之乐不同于人生中通常意义上讲的乐,不是欲望满足或愿望实现后所产生的心理欢快或愉悦,而是人在领悟了生命真谛,经历了人生觉悟后,内心所达到的一种无念虑、无差异、无执著、无绊累、清净自如,圆融无碍的精神境界。如唐朝断际禅师在《传心法要》中所说:"本佛上实无一物,虚通很静,明妙安乐而已。深自语入,直入便是,圆满具足,更无所欠。"
对于此种涅磐之乐,其实不难体会,这是一种心理的圆满自足,无纷无扰的快乐。我们这些凡俗之人之所以时常感到烦恼和痛苦,不能留住间或拥有的欢乐,关键在于我们内心有欲火焚烧,有思虑躁动,有欲此欲彼的冲突,有患得患失的障碍。而一旦有人心灵臻于湛然,超越于一般的是非恩怨,功过成败之外,不为欲念所渍染,不为迷乱变幻的世俗事物所诱惑和烦心,则自然能够享受到安然自足,无露无虑,通达祥和,笃常无碍的精神妙乐。笔者有一位研究理论经济的张姓朋友,此君虽不是佛门中人,但心性寂静。是笔者所仅见的能够在商品化、世俗化大潮中笃定心性,专注于本行,以学术研究为乐的学者。笔者单位的阅览室,这几年可谓门口罗雀,无论研究何种领域的人,都到外面的世界中与市场经济结合去了。张君虽研究的是经济,却不去凑那份热闹,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守在阅览室,人称其为阅览室的"常委"。在物欲世界的诱惑下,笔者的许多同事纷纷耐不住寂寞,心性动摇,看轻看淡了本行事业的价值,以学术研究为苦,相互闲聊起来,皆是心躁气浮,或发财心切,或对时下学子的不良处境满腹牢骚。而张君则不然,他自认学术生涯是他的最佳人生选择和价值所在,阅读和写作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快感与乐趣,平时唯恐时间不足,不能读更多的书,写更多的文章,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追逐社会中的热闹。因此,无论同事中下海的呼声是多么的高涨,无论社会上的其他事业和行道是如何的时髦如何的被捧入云霄,他皆能独坐自足,不为所动,并由此而享受到一份弥足珍贵的不受外界干扰,在学海中静心邀游,潜心体悟,无碍思索的学者之乐。为此笔者常自叹心性太躁,杂念太多,难与此君同乐。但笔者在此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学张君风范,热爱本职工作,不轻易动摇自己的人生志向和事业选择,也许这样在充满障碍的人生中方更能自由通达,身心圆融。
(3)我:涅磐境界中的我不是诸法无我意义上的人我、法我,而是指佛性我。所谓"泥恒不火,佛有真我",就是指佛性我的真实恒在。佛家认为,人身上存在佛性,佛性是世界的本质,也是人性的真如。佛性是真实的恒常存在,因此,人一旦了悟了佛理,真如显现,就能由人我升入佛性我的境界,常葆自我的本真。其实,佛家的涅磐之我有点类似于西方宗教中的灵魂,肉体死了,灵魂仍在,思虑灭寂,人我消失,佛我呈现。但佛性我比人的灵魂自我更具普遍性,是宇宙灵魂的缩影。
佛家在涅磐境界中引进佛性我,目的自然是在于使人蜕去变化无常的为因缘和合所决定的偶然的我、贪欲的我,提升为本然的我、善的我,从而获得生命的超越。没有我的涅磐毕竟不易让人激起向往的热情。诚然,当代人在现实生活中不必刻意去追求一个形而上的我,但佛家以涅磐寂灭来保存我,则无疑对大众的现实人生是有启发和指导意义的。人们在现代社会中所产生的价值失落感、自我失落感、异化感等等,实质上都是人的生命意志受到阻碍所产生的心理危机体验。在生命意志驱使下,人们渴望实现自我、表现自我、维护自我,但在众多欲念的杂扰下,人们往往弄不清自我的真正价值、真正含意和真正需要,从而将自我丢失在忽此忽彼的人生奔忙中。同时,人们也常常企图以有限的身心去涵容、去征服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生中诱人的事物,却总是因为力不从心而感到自我的渺小和沉落。因此,如果我们在这里把追求涅磐境界俗解为不要念念不忘自我、自我价值、自我实现之类意欲勃腾的想法,稳定自己的心性,以淡泊的态度,平常的心性来面对社会和人生,以有常应无常,则或许能够在复杂纷坛,变化繁复,充满异化的世界中维持一种真实的自我。
(4)净:净指无欲染,无烦恼,是佛家涅磐境界最显著的特征。佛家既然以大干世界为红尘滚滚的污浊丑恶之域,则悬为理想目标的涅磐自然应是清净湛然的明澈美善之境。所以佛家在向世人描绘涅磐境界时说它"皆永灭尽,毕竟寂静,究竟清凉,隐没不现",是一种"清净无戏论体",洁净得无"法言说。佛家认为,"世俗之人虽然也有佛性,但为生欲杂念所蒙蔽,所以心灵是不清净的,布满了尘垢,也充满了烦恼。而一,旦趋于涅磐,清净佛性显现,内心澄明,周遍无杂,则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遭遇何种事件,皆能坦然置之,无牵无挂,不留斑点。佛门中有一个故事讲:一天,坦山和尚与一位同门僧人一道外出,在过一条河时,见一年轻女子踌躇于河边,不敢下水。坦山和尚便过去抱着那女子过河。过河后女子远去,同门僧人谴责坦山和尚说,佛门戒色,你怎么能去搂抱那女子呢?坦山回答说,你还抱着那女子呀?我可是早把她放下了。这个故事表明,坦山和尚与那位同门僧人相比,在对佛家意旨的领悟和修为上,实在是高出许多。那僧人虽心中念念不忘格守佛门清规戒律,但内心其实仍有障碍,并未臻于清净无碍之境,因此心中老是存着坦山抱女子的镜头,这无异于他自己的心在抱着那女子。而坦山和尚内心则已达到湛然澄明,空灵寂静的增界,所以虽然有抱女子的行为;却末入于心,与没抱一般。可见,涅磐的清净其实是体现人思虑寂灭的一种品质,也是体现人对外界刺激抗拒能力的一种品质。
佛家的涅磐清净对人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在社会生活中,清净本身就是人们所看重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目标。以我们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为例,外出上下班,莫不饱受大街小巷车水马龙、人流拥挤、五音杂烩、喧嚣闹腾之苦。龟缩家中,宿舍楼,大杂院也不清净,电视声、收录机声、卡拉OK声终日不断,到处都在打桩盖楼,敲墙钉窗,装修房屋,噪音刺耳,令人无可逃避。但这还只是生理刺激意义上的不净。生意场上的竞争,官场上的角逐,情场上的较量,更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使人忙碌心烦。有一位朋友曾告诉笔者,与他在办公室对面而坐的某处长,天天对他耳提面命,谆谆教诲,聒噪不休,让他烦得要命,躲又躲不开。确实,大千世界,红尘滚滚,到处都充满喧嚣,到处都遭受污染,人们欲求清净安宁,却哪里是容人躲藏憩息的清净之地?唯有像佛家要求的那样平息意念骚乱,做到内心清净,气定神闲,泊然无想,方能将外界的侵扰拒之心外,处闹腾之市而不为所烦,居污淖之地而不为所染,使生命挺立如同莲花,洁净安然,层层开出,瓣瓣绽放。
——选自《红尘觉悟·佛法与人生》
第四章《殊胜乐土》之第三篇《让生命化作那朵莲花》
作者 袁阳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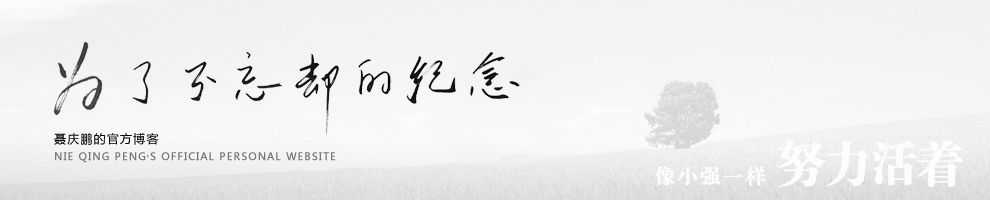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