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晴热。
立秋已多日,夏天过去了。今年的夏天不像往年那样忙,整天和楚涵呆在家里“相依为命”,一天是两顿饭,天天上网上到自然睡,睡觉睡到自然醒,不记得月日,不关心周几,所以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其实休息的时间长了就会发现,闲着容易让人颓废,有点事情做但又别太忙,才是最理想状态。在这样的日子中,时间也并非全是虚度,有两件事情,都曾和夏天有关,而又终与今年这个夏天产生交集。这让我有记录下来的想法。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也许应该强迫自己,赶在遗忘降临之前,写点什么了。
一、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我距离曾经衣袂飘飘的校园时代已经过去整整十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2004年的夏天我们各奔东西,天涯海角,大多数同学和老师都再未见面。QQ上、微信上、校友录上,许多人嚷嚷着聚会。这无疑是一个好事情。不管十年前交情深浅,感情浓淡,虽然没有彼此,十年来生活也已如常,但人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怀念过去,思念故人,并以久别重逢为大喜事之一。老班长M君很早就在操办这件事,联络了各宿舍老大,发了调查表,统计人员,联系酒店,买了纪念品,定了日子。虽然一多半的同学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去,最终也有二十多人成行。7月27日,奔赴十四年前相聚的地方,曲阜。
曲阜是个小城市,但就因为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三年时光,所以脑海里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确确实实有了第二故乡的感觉。至于这三年哪里难忘,竟也说不上来。我想难忘的不是这个城市,而是那三年的大学生活,因为那一切都发生在这个名叫曲阜的县级市,所以一提起这个地方,所有关于那些往事的回忆就会瞬间汇总压缩,升华成一种特殊的感觉,这就是所谓母校。毕业之后也回去过一次,我记得是2006年,M君却说是2005年,不论是哪一年,也已经是八九年之久了。以今天的交通条件,即使不是十年聚会,也是该回去逛一逛的时候了。
聚会的地点选在国铁酒店,我们到得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多。有些到得早的同学,有的出去游览,有的在大堂叙旧,故人相见,分外感慨,或高喊绰号,或激动拥抱,或惊叹胖了、瘦了、没变或者老了,气氛热烈。中午的时候去了学校,昔日的人力三轮车已经改成电动,学校东门那条印象中灰蒙蒙脏兮兮乱糟糟的商业街,也据说因为争创“卫生城市”的原因整饬一新,模糊不似当年的模样。沿街的小摊不见了很多,似乎有些老店还在,看着名字熟悉。曾经吃过的炸串,馄饨,都还在。找了一家饭店,与同宿舍的三个兄弟吃了个午饭,还喝了点啤酒,只花了一百多元,价格比十几年前似乎有些上涨,但还是格外便宜。饭后去了校园,故地重游,从南到北一路走去,爬上了数学楼,看了当年的教室和漆面斑驳的桌椅,都还静静的立在那里。广场上的孔子铜像,已没有记忆中那般高大,同行的B君说:我看孔子胖了。走过了外语楼、科技楼、综合楼和西联教室,走过了图书馆、萃华园、运动场,再穿过北门,走进北公寓,看着当年我们第一批住进的新宿舍,如今也有了老旧的颜色。大家一路走一路说,似乎每一座楼房每一条道路上都曾留下一些故事,那些或欢乐或悲催或傻乎乎的往事今天说来仿佛格外有趣,也仿佛整个大学时代只留下了这些奇特的故事,还深埋于记忆中,至于当时上了什么课学了什么习考了多少分,似乎没人再去提起。故地重游的感慨确实很难说清楚,这就是我的大学,以及大学留给我的。
到晚上的时候,热烈的宴会开始了。当年的老师来了,大家热烈拥抱、合影,推杯换盏。每个人都在讲述着难忘和感动,表达着祝福,此情此景之下,我想最不会喝酒的人可能也有喝一杯的冲动。这确实是欢聚的时刻。酒精让血液沸腾,让思维重组,深藏脑海的往事又被重新提起,当年的酸甜苦辣都成为此刻的谈资,随着一杯杯酒的下肚而转换成甜蜜。一别十载,忽又重聚一堂,大家互有改变,却又一切如故。缘分如此奇妙,大家津津乐道着谁曾恋着谁,谁的绰号的来历,万般心情酒一杯,相聚不易,良宵难得,又何妨一醉。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二、十年生死两茫茫
奶奶去世九年了。按老家风俗,亲人去世头七、三年和十年的时候要有比较大的上坟仪式,家族男女老少都到。而且还有个说法,“十年坟九年上”,意思是十年坟要第九年来上,以表达怀念逝者迫不及待之意。诚然,按照老家风俗,平时的逢年过节,上坟只能男丁去,女眷只有头七、三年和十年坟可以参加。所以像大姑二姑这样的女儿,纵然奶奶已去世九年,也只去坟头上两次而已。所以这是一次隆重的活动。
九年前的农历七月十二日,闷热难耐。八十三岁的奶奶的心脏病发作,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是我毕业工作的第二年,当时还穷困潦倒身无分文,不曾给她尽过一点点孝心。接到噩耗赶回老家的时候她已入殓,棺材盖盖了一半,只露出一角,宽大的寿衣覆盖住她全部身体,我已看不到她的脸。那天似乎是有生以来最炎热的一天,我一路扶着她的棺材,随着送殡的板车到村北的黎山上去埋葬她,一路上汗如雨下。我很庆幸我能陪她走这一程,我恨这路太短,这黎山太近,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就能为她多做点什么了。随着一铲铲的泥土倾进墓穴,她的棺材很快也看不见了,并慢慢隆起一个土丘,她就睡在那里了。后来过了几年,叔伯们商量着给她和爷爷立了一块墓碑,把她微不足道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刻在了石头上。她走了整整九年了,而从我出生,到我二十三岁她走,她给我的,不计其数,我曾给她买过的,就是一张上大学第一年从曲阜带来回来的孔子像挂历,我记得那上面写着几个字“先师孔子行教像”。她让我给挂在屋子里正面墙上很高的地方,她死后的好几年那挂像都在,布满了灰尘和蛛网。再后来她的老宅租给别人住,打扫房子的时候大概扔掉了。她让我深刻的体会着一句古话:子欲养而亲不待。
上坟一切顺利。不像九年前那么炎热,阴天,有小雨,比较凉快。四叔一家来了,大姑一家来了,而且小姑自己也来了。而且竟然是自己记得,自己来的。大姑说,本不想跟她说,她却自己记得,托人打听,然后来了,听说是她孩子的四叔用三轮车送来的,而且来的很早。我见她精神不错,气色也好,说话很有条理,有问有答,只是头发白了多半。她说大女儿结婚了,小儿子在北京打工,而那个法律上的丈夫,还是不见踪影。如果不是到了快吃饭的时候,看到鸡肉端上桌子,她就迫不及待的自己拿筷子去挑肉吃,我都以为她的病完全好了。临走时,她邀请我去家里玩。我确实很想去她家里,也许我有十几二十年没有去过她家里了,这是我的亲姑姑,我们是很亲的亲人,她是病的,但我不是,我是应该去她家里坐一坐的。
关于她的病,我那年写过的《小姑》里的描述,看起来像是聊斋故事。我也怀疑大人们这么跟我说,就像他们说小孩子是外面捡来的一样,未必是真相。这次的席间,父亲喝多了,红着眼睛又说起这个话题,义愤填膺,只是刚刚说起,就被二伯打断了,四叔也沉默不语。这个家族的很多事情还被尘封着,即使我,也暂时无法接近真相。
如果有办法,我想告诉奶奶,九年了,我们都很好。你所挂念的小姑也还好。但是你不在了,我很想你。“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词句完全可以送你最亲最敬爱的你。你死的那天晚上,我和父亲、四叔在你的老屋里睡觉。我没有害怕,迷信说,黑白无常会来领你,或者爷爷会来领你,我都不怕,我希望他们真来,我希望我能看到,再看到你,看到爷爷,看到你有什么可怕的呢,不论是在哪个可能的世界,哪怕在梦里,看到你,都是幸福的。
2014年8月31日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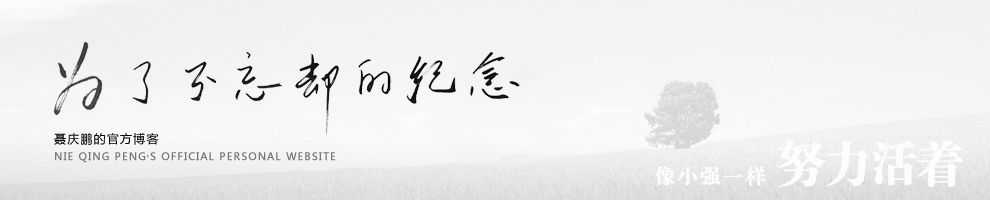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