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下午,朋友开车接我去吃饭,路上我无意之间哼哼了几句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呢》,朋友惊讶的问我:你也听周杰伦?
已经不止一个人这样问过我,而且都是以一种惊奇的口气。最初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和我朝夕相处的老婆,直到我把《青花瓷》放给她听,并很认真的把歌词给她朗读几遍之后,她说了一句:很飘逸。从此我再听周杰伦她便不再惊奇了。
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惊奇,大概是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把自己伪装的过于高深了。前几天的一个傍晚我和一个很漂亮的女同事在学校门口等车,我点了一支烟,她说你也抽烟吗?你不抽烟就够深沉了。我对这个评价有些失望。我不希望给别人留下深沉的印象,因为这不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很天真,天真的像个儿童。这一点我老婆可以作证。
深沉与轻浮相对,一个给人感觉深沉的人必然反对轻浮,而流行元素往往掺杂了太多的轻浮。流行元素有时候也代表一种先进,然而大多数时候仅仅代表庸俗。流行的东西大多数时候都是迎合了低级趣味。而对人们来说低级趣味往往比高级趣味更有趣味,因此流行有他的市场。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流行元素,从未绝迹。而我给别人造成深沉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很少关注或参与流行。
当一个人排斥流行,那必然变得很土。我自己都承认我在生活上是一个很土的人。虽然我从事着互联网这样一个代表着新东西的行业,我仍然在很多方面像一个古董。我不认为“土”是一个贬义词,这是一种风格。是一种可怕的固执。我有时候活在古代,有时候活在虚无的精神中。我永远不愿走进主流社会中,而只能游离于它的边缘。因为我怕极了被包裹,我需要随时逃离。
对与我这样的一个人,似乎不应该知道周杰伦,也不应该哼什么流行歌曲。其实大多数时候我是这样的。但只要活在这个社会上,就不可能把自己与世隔绝。即使我不主动去认识周杰伦,他也早晚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很早就见到这个名字,并知道他很流行。但我第一次在电视里见到这个人并听他的歌,是在2006年的春节后的某一天的下午。当时我在一个即将结婚的朋友家里喝酒。他的妹妹将一张周杰伦的光盘放进VCD里,于是整个下午甚至一直到晚上屋子里都是这个人的歌声。在他的歌声里我们喝了一罐又一罐啤酒,最后都醉了。这天下午我头一次听了《七里香》。我感觉这个音乐很特别。我认识了这个人就是周杰伦。
在很多人看来,我不应该听周杰伦的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年龄。在以我老婆为代表的很多人眼里,周杰伦应该是所谓“90后”或者至少也应该是“85后”喜欢的明星。我作为一个82年出生而且土里土气像个老头子的人,不应该喜欢他的音乐。关于这一点对于许多其他流行歌手来说我是基本认同的,比如那种“遇见蟑螂不怕不怕啦,神经比较大”的歌手,但对于周杰伦,我想不适用。我专门查了这个人的资料,出生于1979年,和我基本上是同龄人。身高和体重也与我相差无几。对于这样一个比我年龄稍大几乎同龄的人来说,我想我们之间不会有太大的隔阂以至于无法理解和沟通。虽然我们的身份、成长环境天壤之别,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我们对音乐和某些人类共有的精神理解上的障碍。所以我听周杰伦的音乐,并在某些歌中获得某些程度的认同感,并由此对他本人进行某些程度的认同,不应该成为一件奇怪的事。
我对音乐完全是外行。对于歌曲和歌手的评价纯粹是从个人好恶的角度出发。但我想歌手与他的歌曲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必然性,歌手的风格决定了歌的风格。歌的品味也反映了歌手的品味。这之间一定是有关系的。虽然娱乐圈不是艺术学院里的练音房,也不是诗人的创作室,身处娱乐圈的歌手难免会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对自己有所改变、妥协以及伪装。虽然存在种种复杂性,但是一个成名的歌手无论其成名的过程如何都必然是在某些方面有出众的才华。我猜想周杰伦一定像他的音乐一样富有才华。他一定是一个有趣的人。
我不追星,我终生都没有崇拜过什么人。对于周杰伦,我同样是通过我听过的为数不多的音乐产生了模糊的第一印象。好在这是一个好印象。如果问我我对他的哪些歌有印象,我细数起来竟然不超过5首。这样的表现肯定不能算他的一个“粉丝”。但是对于我所知道的这几首,我却每一首都印象深刻。
最先是2003年听到的一首《蜗牛》。这是一首让我长久无法释怀的歌曲,虽然数年之后我才知道这首歌是周杰伦唱的。这是一首感情四溢的歌曲,而且还是一首难得的励志歌曲。励志歌曲终于可以不以一种假大空的形式出现,而如此平易近人。虽然他最新的新专辑中有一首《稻香》据说也是励志题材,但也许是风格不同的原因,在我看来比《蜗牛》差之远矣。几乎就是这首歌让我不自觉的把周杰伦和其他流行歌手区别开来。我知道唱过这样一首歌的歌手,一定还有其他歌值得一听。
后来又听过他的《七里香》、《菊花台》等。《七里香》为他赢得了不少奖项,但在我看来这远远不是他的代表作。顶多只是阶段性的代表作。再后来就是《青花瓷》、《说好的幸福呢》,如果说前面几首都是在盛名之下“慕名”而听,后面的两首则是我自己的发现。我发现他的所有作品中只有极为有限的几首能为我所接受,但这几首就足矣。就这几首就足以让我相信,周杰伦,这个流行歌手,这个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应该有这样的成绩,应该有自己的传奇。
我不知道这样啰里啰嗦的一段文字能否解释我之所以听周杰伦的原因。我也不知道以后还是后会继续有人对此抱以惊奇。但我的解释就止于这里了。如果这还不够,我想我可以用周杰伦《青花瓷》里的歌词来做一下补充:“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这分明是一首诗,或者是一幅画,或者是一个故事,或者是瞬间萌发而被准确捕捉和纪录的一段思绪。这般细腻,犹如情人的发丝拂过脸庞,伴随着淡淡的幽香。这样的幽思仅凭文字怎可以传递,于是就需要他的歌声。他似乎就为此而生。
将要结束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似乎对我解释自己为什么听周杰伦有帮助作用:65岁的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先生,在2008年北京大学新年联欢晚会上以老迈、沙哑的嗓音和拗口的普通话演唱了《隐形的翅膀》。我在网上看过这个视频,许智宏先生的声音与甜美的张韶涵自然无法作比,但是我相信每个听众所经历的都是在一种震撼和感动。我也相信许智宏先生此举绝不是一种纯粹的娱乐或者敷衍了事的作秀,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有更好的方式。他的演唱非常认真,这绝不是一个幽默。许智宏表示他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可见流行歌曲、流行文化中也一定包含着优秀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对于流行元素,不论什么样的人都无法全盘否定。
所以,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样的人应该听周杰伦而什么样的人不应该听的问题。当你把周杰伦看做一个歌手,把他的歌看做一种音乐,那么就只存在你是否喜欢这种音乐的问题。这里面没不应该有门第之分。我们不会因为一首歌是谁唱的而喜欢这首歌。我们喜欢的是这首歌而不是它的出身。而所谓出身只是我们在称呼这些歌曲的时候附加的表示符号而已。有时我们会难免爱屋及乌地把喜欢一首歌转化为喜欢唱这首歌的人,这虽然是一种冒失但却无伤大雅。所以对于我听周杰伦,也不应该再有惊奇。也许有一天因为我变了或者他变了,我不再听他。也或者我会更喜欢听他。喜欢一首歌有时就像喜欢一个人一样是找不到理由的。或者找到理由也无法准确表达的。周杰伦只是一个符号,他代表他的音乐。我听的是只是音乐。
2008年12月1日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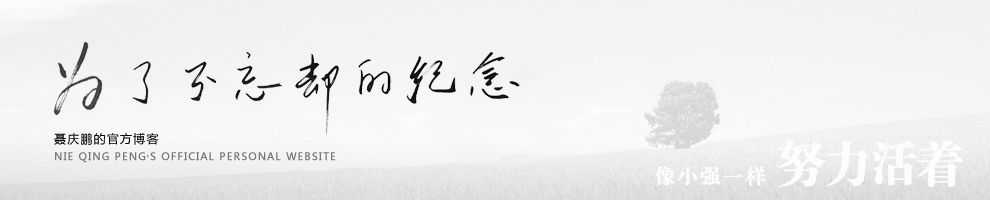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