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六一儿童节。
这个节日不属于我,已经十三年。我最后一次过这个节日,是在一九九四年的六月一日,那天的天也是像今天一样阴沉,还飘着小雨。五年级是毕业班了,面临中考,因此不再参加节日的演出活动。学校遵循惯例,给我们买了一大堆西瓜,堆在教室前面的讲台上,可以随便吃。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吃,那个平时很严厉的袁老师,还有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的度老师,此时也都满脸笑容。没有足够的西瓜刀,于是就用掌和拳头。我不确定我现在是否能够一掌劈开一个西瓜,但那时候确实是劈得开的。女生们要文雅一些,排队用刀,或者抱着西瓜狠狠地在桌子上摔,一般最终也能成功。西瓜大概不算很值钱的东西,但在那时是每届毕业生的盛筵。低年级的学弟学妹们趴在窗户上,馋得直流口水。如果有哥哥姐姐或者认识的伙伴在里面,还有可能从窗户里偷偷摸摸的得到一两块。
从这之后,我上了初中,告别了儿童的节日。虽然每年也都能吃些西瓜,不过像那样豪壮的西瓜盛筵,却再也没有过,大概也不会再有了。
每年的六一天气似乎都不太好。起码在我所度过的五个六一中,几乎每次都下雨。下雨阻挡不了节日的热情,一切还要按计划进行。提前很多天,就要开始排练节目。主要就是唱歌跳舞,还有乐队。我那时候在班里算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分子,也参加过几次演出,记得有一次是说了一段侯耀文的单口相声,相声的名字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最后一句话是:“电影院门口两个老头打起来了!”。排练的时候老师拿了一个录音机,一遍一遍的播放,我就跟着学,那时候大概是二三年级,字也不认识几个,没法记,只能背。最后我竟把这个相声背下来了。到了六一这一天,学校的墙上和教室里都贴上了各种颜色的标语,花花绿绿很有节日气氛。大家都要穿白色的上衣和蓝色的裤子,系红领巾。蓝裤子比较好找,白上衣却难得多,有时候只有一件白上衣,我和姐姐两个人,只能有一个人穿。往往是她让给我。在学校旁边一个园子的大槐树底下,就是舞台了。说是舞台,实际上就是一片平整的空地。全校的孩子们,还有村里的老少爷们,都来看热闹。里面还有我的母亲。后来母亲问我,你在那么多人面前说相声害怕么?我说不害怕,还没上去的时候害怕,上去了就不害怕了,眼前一片空白,台下的人跟没有一样。母亲喃喃地说,那是吓坏了。我不承认是吓得,我确实没有害怕。
以后的几次,演出的地点改到了十里地之外的一个叫大白石小学的地方,两个学校汇演。于是到了六一这天,老师就把我们排成长长的队伍,步行去大白石。一路上敲锣打鼓,很是热闹。陈宝升比较胖壮,经常负责敲最大的那面鼓。那大鼓咚咚的节奏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我一般是吹小号,似乎还做过一次指挥。女生们都发一团花,忘记了是纸剪的还是塑料的,花花绿绿的,拿在手里挥舞,很好看。一路上老师领着高喊口号,那时的口号就是两句话:“学习雷锋,学习赖宁”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学生们如何过六一,是否还喊口号,或者喊着怎样的口号?仔细琢磨一下,口号也有很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吧。
过去了这么些年,孩提时代的事情,能够记起来的已经所剩无几,只有些许零散而模糊的碎片。小的时候盼望着长大,长大后又怀念小时候的纯真。其实怀念也只不过怀念而已,时光的脚步永远向前,不会为任何人改变。既然该来的总是要来,那就早早的到来吧。或许再过几年,我就要为我的孩子过六一节了。可能他已经不再需要一件白上衣和蓝裤子,也不会再喊“学习雷锋,学习赖宁”。父母生下了我,让我有了至今怀念的童年,那我也应该给他,我将来的孩子,一个值得怀念的童年。一代一代人,也许就是这样,轮回吧。
天下的孩子们,不论是蓝天下的,阳光下的,父母怀抱中的,还是战火中的,血泪中的,孤独地踯躅于街头的,祝你们,节日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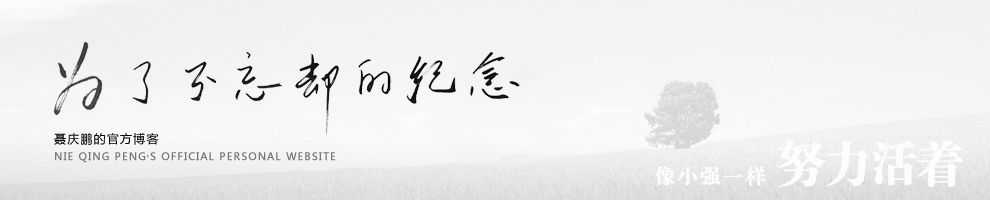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