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坐公交上班,途经大学城。在某大学门口,看见聚了一群人,有男有女,拉着几条横幅,白底黑字写着标语,大意是学校欠了他们的工钱,已经欠了好几年,至今要不到钱。我脑子中立马浮现出一个词:讨薪。
“讨薪”这个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不过肯定时间不长。输入法中还拼不出这个词,可见也是个近几年的新生事物。“讨薪”其实就是“要债”。可能是感觉要债不好听,精英们想出了“讨薪”这么个词。不过我对“讨”这个字印象不好。好像乞丐一样。按照千百年来古今中外都通行的法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而不料到了今天,事情却要颠倒,欠债有理,讨债无门。欠债的理直气壮,要债的唯唯诺诺。我依稀记得白毛女中杨白劳就是欠了黄世仁的钱,才让人把闺女抢了去。因为欠债还债逼债弄得家败业破卖老婆孩子的故事也不少。但无论如何是是非非悲悲惨惨,但是大体还是偏离不了大的法则。
不过这些年目睹的桩桩现状,却多是相反。跳楼讨薪、拦路讨薪、挂牌讨薪、卖欠条讨薪的怪现状频频上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像拉着横幅抗议这种方式,已经是这些讨薪方式中最文明的了。而这些讨薪的结果,真正讨到钱的少,被打、被抓和不了了之的多,有的还搞成了人间惨剧。前天还刚刚看到一则十七年前民工要工资被打残扔到外省乞讨为生的事,而且很不幸这就发生在日照。这件事情的真假目前还没有查清。如果是真的,那我想可以作为“暴力欠薪”的最早明证了吧。于这些新闻相对的是,从没有听说哪个欠债的人要跳楼要上吊或者被打被杀的。看来文明社会就是好,像杨白劳那种欠债被人抢走闺女的是是不会发生了。不过法制保护了欠债人,却没能给债主更好的保护。
对于“欠薪”,应该至少分成两种:无奈欠薪和恶意欠薪。前者是没钱可还,后者是有钱不还。如果所有的欠薪都是后一种情况,那么解决起来应该就容易的多。其实在之前我也是很不理解这些欠钱不还的“大老板”的。没钱能盖大楼么?但是这些年的耳闻目睹,使我逐渐相信没钱也是可以盖楼的。楼盖起来了,钱没着落。于是建设方欠着施工方,施工方欠着材料方和包工头,包工头欠着农民工——这一连串下来,处在中间环节的人既是债主也是欠债人,心里倒还是有底的。而最底层的农民工没底了,看不到钱,什么都是零。我也明白了盖一座大楼不像在菜市场买菜,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一座大楼动辄几百几千万,这么一笔钱往往不知道多少次、多少年才能拿到。这样的数字和机制足以拖垮一个建筑公司,也足以让成百上千的建筑工人(建筑工人的称呼都不准确,因为在中国他们叫农民工)长时间苦苦等候,甚至有些人一无所获。在这样的“无钱可还”面前,似乎逼谁都没用,钱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但是在这样的看似“三角债”的窘境中,最受害的还是农民工,因为农民工并不处于这个三角循环中。
有欠薪就有讨薪。每每有各种“非常规”甚至偏激的讨薪行为发生,呼唤理智、冷静、走法律途径的声音就会响起。但是但凡用脑子去想一想就能知道,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如果不是所谓法律途径困难、低效、高成本,以及判决书如同废纸,如果不是他们在社会底层挣扎没有经济地位也没有政治地位也没有人给他们鼓与呼,谁会去采用鱼死网破的方法?谁会走上破罐子破摔的道路,谁会拿出舍得一身剐的勇气?谁会撕开面子甚至动刀动枪?农民工在当今社会是无可辩驳的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他们就像一群温顺的羔羊,任人宰割,只要还有一条活路就不会反抗。但是如果最后连苦力钱都要剥夺,那愤怒的羔羊也会反抗——哪怕是用仅剩的近似自杀的方式——可悲而又残酷的方式。
不过事情也并没有那么复杂。当前的各种“讨薪”事件和“欠薪”纠纷,绝大多数都发生在建筑领域。其他领域则鲜有耳闻。如果能够解决掉建筑领域的欠薪问题,这种中国式“讨薪”就可以少上演甚至不上演。其实这个话题也早已不是一个新话题,记得从2004年温总理为民工讨工钱的时候起,全国整顿建筑行业拖欠农工工资的活动就轰轰烈烈的展开了。这四年来应该说是有成绩的。但是距离事情的根本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各地各种形式的非常规讨薪行为仍然时常上演,这些事件的主角都是出卖苦力的农民工,而受害者也往往都是他们。这是无论如何都让人接受不了的,也是政府在将来一段时间内仍然需要继续重视和关注的。其实完全还可以有更强有力的措施和更有效的手段,就看我们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有多重视和多大的决心。
在面对“讨薪”的时候,我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就站到讨薪者这一边。大概人天生就有同情弱者的怜悯之心。但是除此之外,我对农民和农民工,还有着特殊的感情。我视他们如自己的亲人,我经常观察他们,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像我的父亲或者我的兄弟。因为我父亲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今年55岁了。在城市里已经是退休的年龄,但是还是要在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和20出头的棒小伙子一起干活。村子里60岁以上的仍然干建筑队的也大有人在。并不是他们天生就喜爱这样的辛苦劳动,他们也本不该天生就从事这样的劳动。但是命运,和特殊的历史阶段,和天生的忍耶和淳朴,和生活的压力强加给他们这一切。他们已经选择了默默承受,那就请把他们那应得的一点点微薄的血汗钱,及时交到他们手中。这不是对他们的怜悯和施舍,而是对他们付出的辛苦劳动的最起码回报。
现在很讲究“换位思考”。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经理们、老总们、政府官员们和决策者们,也不妨设身处地的换换位置,凭心而论地想一想:但凡还有第二条更好的路,谁会选择这样一个靠出卖体力和汗珠子挣钱的行业?面对这样的一群人,实在不应该忍心,让他们一再登上以各种悲壮的方式,“乞讨”自己的劳动所得。
2008年1月14日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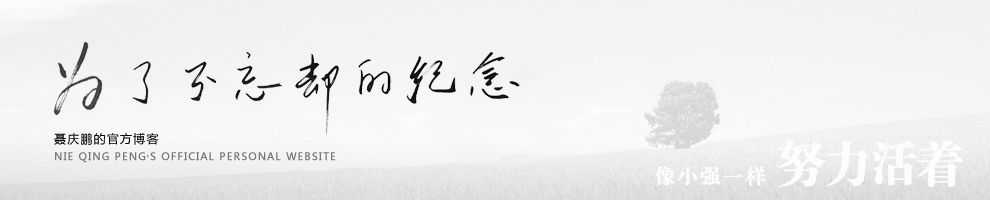

看过您写的,当真有些气愤,跟你一样呀,当我看到日照"十七年前民工要工资被打残扔到外省乞讨为生的事"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也不是不敢相信,而确切的说是不想去信,不想摸去心中美好的形象.
另一种声音:
“殇”看到这个字自然让人想到死亡,聂老弟用这个字来定位“乞薪”,思想之深远,见地之精准,痛心疾首之表情跃然浮现,同为80后的为兄自叹不如,在这个漫天飞舞形容词砌墙,名词做动词的时代里,居然还有如此出污泥而不染的聂老弟,80后幸甚,聂老弟之思想见地实为我辈之楷模。
虽是如此,“乞薪”之现象则非某个领域就能解决之,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之产物,我辈虽痛心疾首却也享受“讨薪”族的劳动,然现代经济体制不断进步,社会不断发展,“工”“薪”之矛盾也在不断缓解,国家也积极出台政策调控。
社会是复杂的,现象是存在的,发感慨实属正常,然我辈身兼祖国未来之大计,应以积极之心态应对社会现象。换一种角度思考或许更能发现社会的美好。我们的生活不还是得过吗?诚如聂老弟所言“8年前逃离了八亿”更多的八亿逃离八亿,那八亿就会另一种样子。
农民社会医疗保险正在推进,政府1号文件也是扶持八亿、现在提倡的工业反哺农业、一直到小麦直补,直至目前的养猪补贴…..,虽然此刻政策的倾斜远不能解决八亿的实际问题,但是这表明了国家的一种姿态,表明了一种努力趋势,八年前聂老弟在无人知晓的小村子里忍受着家境贫寒,姐姐过早辍学,八年后却在一个新兴的城市里立足发展,携娇妻之手共画美好未来,这些不都是社会的变化吗?我辈应该相信,也应该看到未来之光明….
to:佚名
兄台说的很对,思考问题也非常全面,也不乏深度。愚弟受教了!
不过我与您的不同之处大概就在于,我从骨子里十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本人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尤其对于生活,是充满信心的。但是对于这个社会的审视,我却是悲观的。这种悲观来自很多方面,从根本上说可能是一种“恨铁不成钢”。诚如兄台所言,近些年来,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在进步,在改善,在提高,在向着更加合理和理想的方向发展。但是速度还不够快,力度还不够大,措施还不够硬,决心还不够坚定。很多应该引起重视的事还没有被引起重视,很多应该早就的解决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很多应当改变的不公平和不合理仍然存在……面对这种情况,乐观主义者可能相信这些问题在未来能够解决,他们是相信未来的。但是悲观主义者,尤其是完美主义者(或者理想主义者),他们在任何时刻都保持悲观——或者说冷静。他们的眼睛永远盯着社会的黑暗面。这是因为他们太执着于光明,任何黑暗的存在都会另他们不满,这也就是他们始终“牢骚满腹”的原因。但是两者相同的是,两者都是相信未来的。我想悲观主义者的存在是有价值的,他们似乎是消极的,他们自己的力量可能是不能改变任何东西的,但他们的存在能够发现和放大社会的黑暗面,以影响、劝服直至启迪更多的人,去改变。
在今天的太平盛世中,完全可以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去歌舞升平,但是也需要有百分之一的人站在一边泼冷水——这样才不至于盲目乐观。盲目乐观和盲目悲观都是无益的,在这一点上,两者都是需要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影响的。
另外,这个博客快两年了,来的人不少,留言的不多。留言中真正发表自己的深刻见解——尤其是提出批评的,更是少之又少。我非常感谢您的诚恳,也非常佩服您的睿智。期待与您更多的交流。
聂庆鹏 1月17日夜
刚从单位回来,无意又看见了你的回复,倍感荣幸,社会进步的动力来自矛盾的产生及解决的过程,你我的思想也在辨证中进步,认识你非常荣幸,你让我看到了被称作浮躁一代中的理智面,或许我们都长大了。真正长大了。